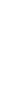年少的他第一眼便瞧见房内那只貍花猫1。
猫花猫蹲伏在炕上,头脸俯贴炕面,深深埋在前爪里,脑袋只从头顶心露起,两只尖尖耳朵朝下歪。
“世子爷,怎地一直盯着炕上?”炕的另一端,一个姑娘缝着棉布抹额。
赵玦问道:“霜降姐姐,这猫怎么了?”
霜降放下针线,下炕瞧向貍花猫:“没怎么啊?”
赵玦道:“它这模样像极孩子挨骂,没脸见人,或者倒地大哭。”
霜降噗嗤一笑:“它在睡觉。”
“猫是这种睡法?”
“你只爱猎鹰、猎犬和骏马,难怪不知道。猫爱晒太阳,冬日难得出大太阳,自然要晒上一晒。可日光映着积雪又太亮,它只好这般遮住眼。”
“原来如此。——你伤风感冒,告假在家,怎不好生休养,还在做针线?”
霜降笑道:“劳碌命,闲不住。——其实我好了大半,早想回房里伺候,我娘偏不许,说万一将病气过给你,必要打折我的腿。”
她掏出手绢将炕上细细掸过,向赵玦让:“你请上炕,我取茶水去。”
“你人在病中,不必麻烦,让小丫头来。”
霜降将火盆挪近赵玦,笑道:“丫头出去了,就算她在,进京以来,王爷王妃便千叮咛万交代,你的饮食绝不能让外人经手。”
赵玦上炕,拿起炕桌上的棉布抹额瞧,问道:“霜降姐姐,这是预备孝敬你未来婆婆邝大娘的?”
“是做给我娘的,你也晓得,天冷她就犯头风,总不能根治。戴上抹额暖和些,能缓和疼痛。”
“为何不用绸面,你若短少布料,我……”
“你别再送了,她得了好东西从来舍不得用,全添进我嫁妆里。因此我拿棉布作抹额,料子便宜,不好作嫁妆,我娘只能留下自个儿戴。”
赵玦道:“我再打听打听京城有哪些大夫擅长治头风,京城人才辈出,就不信一个圣手都没有。”
“又要偏劳世子爷,多谢。”
赵玦道:“应该的,奶娘对我有哺育之恩。”
霜降叹道:“我娘常说自己命薄,自小飘零,幸好遇上王府这等宽厚人家,不嫌我们孤儿寡母命硬,让我们都进你房里伺候。等你用不着奶娘了,王妃娘娘又将我娘调到她身边管事。”
赵玦由“命硬”二字思及术士吴神仙批命他“有命无运,刑克父母”,难得不庄重地撇了撇嘴:“命数之说虚无飘渺,如何能信?”
霜降道:“王府待我们娘儿俩的恩德不止这桩呢,我们签卖身死契,原无赎身的理,可我娘开口求情,王爷王妃便将我放良,好自主婚配。”
赵玦道:“我们因为皇曾祖病笃,由边疆被召回京城,现如今他老人家已经龙驭宾天大半年,我们还留在这儿,不知几时能走。你若不曾随行,留在陇阳,这会儿早成亲了。”
霜降正色道:“王府于我们有再生之恩,天涯海角我们都当追随左右,尽心侍奉。横竖王爷辖管陇阳,我仗着王府狐假虎威,晚个一年半载成亲,邝家也不敢有二话。”
赵玦沉吟半晌,道:“也不知一年半载之后,能不能回陇阳。”
霜降忙问:“怎么,世子爷听到什么风声了?”
赵玦摇头:“不必听到风声,叁皇叔……”他不大情愿改口,“今上至今对父王全无差使安排,也不放回陇阳,任他闲赋在府,只怕要将他长留京城。”
霜降压低叹息:“没想到是今上继位,府里全当太宗皇帝幽禁了宁王爷,就会按照宗法来,传位给我们王爷。”
“皇曾祖提防父王,”赵玦说时,年少面庞露出早慧不可避免的忧悒,“父王因为四皇叔长年受冷落,皇曾祖恐怕他一朝得势要为难四皇叔,丝毫不考虑……”
丝毫不考虑叁皇叔安王以资质和表现皆平庸的庶出孙子身份继承大统,也容不下他父王这个无论在宗法和功绩上,承祧都更名正言顺的嫡长孙。
他向霜降道:“你是我的同乳姐妹2,情同手足,这些心事只能对你说。”
窗外有人问道:“霜姐儿,家里来客人?”
霜降隔窗道:“娘,世子爷来了。”
“奶娘。”赵玦按照礼法大可坐着不动,仍旧下炕迎人。
林嬷嬷进得房来,面上堆笑向赵玦嘘寒问暖,转头对霜降皱眉,眉间原有的悬针纹凹陷更深。
“霜姐儿,你服侍世子爷几年了,怎地还这般粗心大意?时气寒冷,火盆里的火不够旺,还不快拿火筯拨一拨?倘或冻着世子爷,仔细你的皮。——真是,跟你那短命老子一般缺心眼。”
霜降唯唯诺诺,悄悄向赵玦嘟囔:“我娘就知道心疼世子爷你,不管她病了的女儿冻没冻着。”
赵玦道:“奶娘再疼我,我也越不过你,你是她嫡嫡亲亲的女儿。”
他留意林嬷嬷气色不佳,因问道,“奶娘有烦心事?”
林嬷嬷瞧了他少顷,涩声道:“王妃娘娘房里的周嬷嬷卷了细软想逃被逮到,教娘娘下令杖毙。”
赵玦吃惊:“我母妃待下人素来宽和,那周嬷嬷也一直忠心耿耿。”
林嬷嬷忙道:“世子爷你年少,哪里知道人心隔肚皮,到兵荒马乱时节才分得出是人是鬼。最近有些下人忒不像样,佛都有火,王妃娘娘很该狠狠收拾,要不,一个个都上房揭瓦了。”
那阵子,赵玦旁观母妃御下渐渐严厉,但治标不治本。义德帝存心干晾他的父王,府里不乏下人赤心侍主,不离不弃,也有许多下人生了离意。
王府人心浮动,他的父王倒是沉着,每日晨起练武强身,余下工夫莳花种草,吟诗作赋,念佛抄经。
赵玦只道父王久惯征战沙场,练出临危不惧的修养,直至某日,他在屋外听到父王叹息。
原来父王并非不忧心,只是身为王府主心骨,不论内里如何煎熬都不能形于色,否则府里将乱成一团。
他也开始勤于念佛抄经,冀望苍天开眼,保佑全家平安。
不久情势急转直下,言官以周嬷嬷遭杖毙一事,弹劾襄王府刑罚过当,草菅人命。事情一旦起头,朝内对他父王的弹劾跟开了闸似的,一波接一波。
终于一日,赵玦听父王透露,要在翌日将他们母子悄悄送出京城,人手和行程皆安排停当。
赵玦道:“父王,孩儿不走。”
他的父王口气温和,但不容商议:“你必须走,若非形势不妙,我断不会出此下策,让你们母子亡命天涯。”
“难道再无转寰余地?”
“朝臣弹劾我,连贪墨军饷,杀良冒功的罪名都列了,这是要将我抹黑到底,方便赵昂动手。”
赵玦听得父王不顾礼法,直呼义德帝名讳,意识父王和叁皇叔即将公然反目。
“父王,我们一块儿走!”他求道。
他的父王温声道:“阿欢,你关心则乱了。”
赵玦猛省自己说了傻话,义德帝视他的父王为心头大患,岂能容他逃走?
他的父王亦道:“我逃了,赵昂必定翻天覆地追捕;我留下,你们娘儿俩逃走,追捕阵仗兴许小些,你们便有一线生机。”
“孩儿想和父王同患难。”
“你留下,不过坐以待毙,正中赵昂下怀,轻易将我们全家一网打尽,徒令亲者痛,仇者快。”
他的父王好说歹说,他略有动摇,因问道:“母妃肯答应吗?”
“她还不知情。今儿她刚由相国寺礼佛回府,累了一天,正在休息,到晚夕我再和她说。”
父子俩相对无言,许久父王露出一丝苦笑:“我自幼在你皇曾祖跟前便不如意,因此立心绝不让儿女步自己后尘,必要让他们活得比我欢快肆意,可惜……”
赵玦明白父王含蓄指出皇曾祖偏疼四皇叔宁王,令他从小郁郁寡欢。
他心知礼法人伦不允许,还是恨起他的皇曾祖处事不公,生生害得他父王龙困浅滩被犬欺,一家骨肉分离。
是那时母妃翩然来到,笑盈盈道:“你们父子俩都在啊。”
王府内忧外患,人事纷扰,他的母妃恒常妆饰得体,容光鲜妍。
父王问道:“你不是在房里休息?”
母妃笑道:“只是烧香礼佛回来,又不曾大动干戈,哪里就累到得休养生息了?冬日酷寒,我熬了补药给你。阿欢,你那份我打发人送去你居院,让霜降熬煎。”
赵玦回到他的居院,便有林嬷嬷呈上补药。
他吃了一口,面露疑惑。
补药汤色深,药味却淡,肉味反倒浓重。
林嬷嬷见状问道:“世子爷,怎么了?”
霜降立在林嬷嬷后头,问道:“世子爷可是嘴苦?待会儿吃完药,用点蜜脯过口。”一边说,一边打眼色。
“良药苦口。”林嬷嬷道,“世子爷,趁热吃吧。”
赵玦料想霜降必有正经缘故,便不理论,将药吃完。
及至林嬷嬷离开,赵玦向霜降问起究竟。
霜降道:“世子爷,多谢你帮忙遮掩。近来我娘甚是心烦气躁,动不动便唠叨骂人。方才我盛药汤,不小心打翻大半,教我娘知道,定要惹来好骂。幸亏早先我炖了黑豆炖鸡汤,便趁娘眼错不见,搀了鸡汤进去。”
赵玦道:“你也太小心了,奶娘的脾气你还不清楚?她对你就是刀子口,豆腐心。”
霜降不知想到什么,红了眼眶:“是,她嘴头子厉害,心里全是为我打算。”
那夜,赵玦在居院设香案,焚香祝祷:“天地神佛在上,善男赵世玦一家不幸,遭逢奸人当道,父亲忠孝报国,空落得有志难伸,有冤难诉。上天垂怜,保佑弟子父母渡过此劫,弟子愿以性命换取父母重回陇阳,平安终老。3”
哪承望深夜里,锦衣卫登门宣旨,道是襄王交通外敌,即刻查抄王府,并将襄王及其世子提取回衙。
他的父王原本沉得住气,听闻锦衣卫要连同他一并带回诏狱,立时翻脸。
王府里本来就守备得如同铁桶一般紧,父王发出暗号,府里各处亲卫同时发难,将入府的锦衣卫尽数歼灭。
只是锦衣卫在府外也布下重重兵力,他们一家无法突围。
王府亲卫与锦衣卫相互攻防,渐有死伤。锦衣卫堂官见久攻不进,下令火攻。弓箭手往王府射入火箭,府中多处窜起火苗,烟薰火燎。
混乱中,赵玦得知霜降死讯。
“林嬷嬷母女偷开角门迎入官兵,教府中侍卫发现,霜降教人乱刀砍死,林嬷嬷不知躲哪儿去了。”下人如此禀道。
赵玦不信,他与林嬷嬷母女名为主仆,然而生来便亲厚如一家,她们怎会吃里扒外?
一个亲卫寻来,道:“世子爷,王爷殿下请你速去正厅议事。”
赵玦一刻不耽搁赶到正厅,他的父王坐在厅里,手搁在脉枕上,面色青白,正自发怔,府里首领太监齐奉在旁侍立。
赵玦奔上前,问道:“父王受伤了?”
他的父王由椅上立起:“阿欢坐下,让齐奉为你把脉。”
齐奉不只统领王府内院宦官,还精通歧黄之术。
赵玦脑子一时转不过来,兵荒马乱时节,正该奋勇杀敌,哪得工夫做这不急之务?
“阿欢,坐下把脉。”他的父王再度吩咐,神气十分严肃。
赵玦遂依言而行,齐奉把脉之后,禀道:“回禀殿下,世子爷也中了毒,不过较殿下轻微。”
他的父王眼睛一亮:“如此,阿欢还有救?”
“这……此毒药性霸道,即令服用些许,终不免折损元气,寿元大减。”
父王神色难以形容,说不出地悲愤苍凉。
“我还指望虎毒不食子……”他顿了顿,问向齐奉,“你可否估算世子寿元剩下几何?”
“若善加保养,约莫能拖上一二十年。”齐奉说归说,口气并无十足把握,“此后世子爷若过于劳累,便可能忽然脱力昏迷,耗损元气更甚。”
赵玦越听越不吉,因问道:“父王,究竟怎么回事?”
他的父王拿起桌上一张桑皮纸,纸张单薄,散发药香,不问可知包过药材。
如此寻常轻巧的纸张让他的父王拿着,居然拿得手抖——他那平日能轻易提起几十斤长鎗的父王。
父王话声也在发颤:“今日你我吃的补药有毒,服下此毒,五脏六腑迅速衰败,不出数日无疾而终。”
这话好似在人头顶打了个焦雷,赵玦问道:“父王,是谁下毒?”
他的父王不答话,喃喃道:“我哪里对不起她?”口气萧索,眼眸空洞。
赵玦心跳急了起来,这世上能教他父王灰心丧志的人屈指可数。
他起了一个模糊而可怕的猜想,即使不愿深思,终究必须问个明白:“谁是凶手?”
父王道出他最恐惧的答案:“你的母亲。”
“不可能!”赵玦嘶声道,“定是奸人挑拨,父王切莫轻信。”
他的父王怜惜看着他:“阿欢,王府覆灭在即,旁人挑拨我们夫妻,有何益处?”
赵玦始终不能相信:“母妃谋害我们父子,又有何益处?”
“她和赵昂做了买卖,药死我们父子,布置成畏罪自尽,换取她带上王府产业全身而退。今晚她听我透露私逃安排,便连夜向赵昂通风报信。”
“父王从何得知这些内情?”赵玦问道。
当他听毕父王解释和嘱咐,毛骨森然。
“阿欢,”他的父王交代,“王府将破,我先回居处,你待会儿立刻跟来。”
赵玦像作梦一样来到父母居院,途中意外受流箭所伤。
在居院里,父王依照先前在正厅的谋划,作势要杀母妃,母妃挣扎呼救。
赵玦拎弓上前,道:“父王,放过母妃!
——在正厅,父王要他唱和作戏,扮白脸救下母妃,放箭弑父。
赵玦举弓搭箭,大喊道:“父王,放母妃走!”
——父王说,我身中剧毒,已无生望。纵使今日不死,下诏狱一样不得活,不如拿这条残命换你生路。父王死在你手里,也好过教赵昂折辱毙命。
赵玦喊道:“父王住手,我放箭了!”
——父王说,赵昂阴险卑鄙,见我们父子自相残杀,他心中得意,或许肯饶你性命,留下你当成我不如他的见证。你又救了你母妃一命,但愿她善念未泯,肯帮你求情。阿欢,父王盼你觅得转机活下去。
赵玦放声大叫:“父王!”
在这声叫唤中,他放出了箭矢。
他以父王手把手教导他的箭法,放出了箭矢,射穿父王的胸膛。
铿锵的刀枪声,惶急的人声,红亮的火光,刺鼻的烟味,翻飞的雪花,一切通通消失了。
天地刹那虚无静谧。
赵玦眼睁睁看着他的母妃自顾自逃离,彻底坐实抛夫弃子,独自求生。
他顾不上追究,奔到父王跟前,目睹自己曾经意气风发,豪气干云的父亲跪在地上,精气神迅速颓靡,英雄末路。
忽然父王无声笑了,彷佛在自嘲:这一生一世,究竟算什么?
而后父王看向他,温柔痛惜。
“阿欢……对不住……”父王说着,咬牙掏出匕首,刺进他胸口,拼尽余力完成父子相残的苦肉计,“没能让你过上……更好的……人……生……”
父王话音方落,气力衰绝,倒向他怀里。他撑不住,带着父王一起倒地。
他仰躺在冷硬的青砖雪地上,胸中插着森森利刃,遥望无穷无尽漆黑苍穹。
为什么我们父子要遇上这种事?他茫然自问。
夜空下雪花乱飞,洁白的雪粒在暗夜微发莹光,伴随凛风漫天落下,彷佛星子纷纷坠地,教人错觉天崩地摧。
四面八方金革相击,靴声橐橐,大匹人马络绎不绝涌入,往此处逼近。
赵玦怔怔忖道,锦衣卫很快就要找来了。
那么神呢?
朔风大雪中,他轻抚倒在自己身上的父王,再探不着温度,而母妃不知远远逃往何处。
从此以后,剩下他一人独活。
泪水由眼眶滑落肌肤,在隆冬寒夜里迅速凝结成冰柱。
他感觉不到面上寒意,独独疑问一件事。
神在哪里?
究竟在哪里?
赵玦霍地睁开双眸,从梦中醒来,眨眼工夫,他辨出自己躺在居处退思斋。
身上那股虚弱乏力太过熟悉,他意识自己又发病了。
下一瞬,他记起发病前因,大惊坐起。
“小村姑!”他唤道。
原婉然趁夜逃跑,教他关在园子后门附近的柴房,不久地动了。
“原娘子呢?”赵玦质问守在床畔的赵忠,强自支撑下地穿鞋。
“小的不曾留意。”赵忠回禀。
原婉然将他家二爷气到发病,他管她死活做什么?
他又道:“二爷,请留下将养,小的这便派人过去查问。”
赵玦不搭理,风急火急出房。
赵忠快步跟上,将斗篷往赵玦身上披,生怕他病后吹风着凉。
赵玦走不多远,暗恨病后虚乏走不快,再顾不上要强,自行将手架上赵忠肩颈,让他搀扶自己。
却听赵忠禀道:“二爷,原娘子逃跑的事没捂住。”
赵玦目露寒光:“是那茶房婆子多口?”转念又觉不可能,他在原婉然逃跑沿路预作防备,将动静掩盖得滴水不漏,包括调了嘴紧的下人在附近一带上夜。
也不会是原婉然房里丫鬟走漏风声,她们早经吩咐,遇事先行遮掩,同时上报退思斋,静候示下,断然不敢擅自声张。
赵忠道:“是流霞榭的丫鬟。”
他续道:“粗使丫鬟晨起小解遇上地动,跑进正房叫大丫鬟逃命,又进寝间叫原娘子。但房里无人,床上被子迭得整齐,她便嚷嚷原娘子失踪,满院都听见。”
赵玦沉着脸前行,赵忠道:“林嬷嬷迟早得到消息,定要落井下石,二爷倘使再坚持保住原娘子,德妃娘娘那儿……”
“我自有道理。”赵玦强硬打岔,铁了心不听进言,赵忠只得作罢。
主仆俩紧赶慢赶赶到茶房,双双怔愣。
继而赵忠面露喜色,赵玦却是脸色煞白,好似回到他父王横死那夜,天地寒峭刺骨。
茶房一排大房子经历地动,塌成一座座小山也似的碎砖瓦堆。
赵玦挣开赵忠,跌趺撞撞往前奔。
“小村姑!”他喊道,认出茶房原先位置,停在近处一座高低大小可能埋了人的瓦砾堆之前,飞快搬开碎瓦。
屋瓦碎片锋利,他赤手搬挪,没几下便割出数道口子,一时血流如注,染红双手,血水洒落在砖块碎瓦上。
赵玦浑然不觉,疯了一样只管搬物,心中不住呐喊。
别再带走她,求求祢,别再带走她!
当赵忠回神阻拦,短短工夫,赵玦已满手伤痕。
“二爷,你受伤了!”赵忠将主子由瓦砾堆前拉开。
赵玦推开他,红了眼继续搬物。
赵忠道:“二爷,原娘子虽在这片废瓦之下,却不知人在何处。你盲目搬挖不但救不出她,还要伤着手。”
一句话提醒赵玦,他喝令:“带嗷呜过来!”
他由眼角余光瞥见园里下人叁叁两两将欲走来,又下令:“调我亲随过来搬砖瓦,拨人守住周围,不准闲杂人等靠近。”
嗷呜一教人抱到茶房,便跳下地到处找原婉然——它在空气中闻得到她的气味。
不多时,它发出呜呜鼻呜。
明明原婉然的气味就在近处,它却看不到人。此外它嗅出了血气,不只是血水味道,还有脏腑残碎所散发的腥味。
嗷呜直觉原婉然出事了。
赵玦道:“嗷呜,找你主人。”
不等赵玦下令,嗷呜已跑上瓦砾堆,耸起鼻子这里嗅嗅,那里闻闻,很快跑到一块废瓦隆起处哀声大叫。
赵玦的亲随小心搬开石块瓦砾,赵玦在旁等待并上药,彷佛过了千万年那么久,终于有亲随发声喊:“找到人了!”
他们在几根交错倒落的梁柱下发现原婉然,她倒在柴堆旁,柴堆恰好扛住梁柱,架出一块地儿让她得以容身呼吸,并且多多少少挡下塌落的屋瓦。
赵玦赶到原婉然身畔蹲下端详,她浑身厚厚积了一层灰,压了好些碎瓦,肚腹处一团血迹洇透灰尘,隐隐血肉模糊。
他飞快卸下斗篷,将原婉然从头脸覆盖全身,轻轻抱起。
“原娘子仙游了,”他向左右说道,“暗香阁离这儿近,就放她在那儿停灵。”
_φ(-w-`_)_φ(-w-`_)作者留言分隔线_φ(-w-`_)_φ(-w-`_)
1这章的貍花猫就是第二零四章提过的貍花猫
2乳娘的孩子和她哺育的孩子被称为“同乳兄弟姐妹”,《红楼梦》里,贾琏和王熙凤叫贾琏奶娘的儿子“奶哥哥”
3赵玦原名赵世玦,在皇家,他这一代用“世”字为名字中的上字,下字则由父母决定。当他被废为庶人,按大夏礼制,不能再用“世”字,故改名为赵玦
4王府覆灭详情在第二叁七章,赵玦父王襄王原本在正房堂屋中箭,因应这章叙事,将场景修到户外。还有上章的章节名称跟旧章重覆,为免混淆,新章改成“我想回家”
5婉婉得益于柴堆支撑和梁柱遮挡,获得避难空间。这个空间可以说是黄金叁角,但现实中,黄金叁角虽然不是绝对不可能发生,却已被普遍认为是错误无用,说来话长,详情请大家自行搜索。总之,文中这个细节大家看看就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