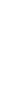她极力扼抑手指颤抖,缓缓松开身上绑带,矮下身让嗷呜由她背上跳落。
“嗷呜没跟着我,”她向赵玦低声下气,“是我将它绑来。”
赵玦不置可否,朝通往园子的角门让:“回去吧。”
原婉然转头瞥向那道仅剩数步之遥,通往街上的角门,以及门上铜锁,心中十分不甘,到底只能忍住眼泪回园。
赵玦早作调度,当下从院里到园子的角门沿途大开,原婉然花了许久工夫好容易出了园子走到外宅,没花多久便要走完回程。
事已至此,她肚里盘算如何“陪罪”平息赵玦肝火,及至走到园子附近,远远见了园门,双腿灌铅似地定住脚——当真又要回到牢中牢,笼中笼了。
赵玦等了她一会儿,方道:“走吧。”
原婉然出声答应,迈开腿脚却一步挪不了叁寸,委实不愿往牢里越走越深。
赵忠在旁木着脸,心里极不以为然。
他家二爷彻夜未眠,又动了一番气恼,在在伤身,正该回居处歇息,原婉然偏还拖拖拉拉。
赵忠心烦不耐,握持火炬的手不觉动了动。
嗷呜依在原婉然裙畔,它的智识不足以明白主人为何整宿背着它上天下地,但凭本能感知出四周氛围诡异,主人心绪忧惧,回程便紧跟她身侧。
当赵忠手中火炬火苗摇摆,光影闪动格外分明。嗷呜警惕留心,直觉赵忠对原婉然没好气,便朝他低狺,走到自家主人身前作势护卫。
原婉然不明所以,但见嗷呜半大不小的身躯挡住自己,要将远处的赵忠隔开,鼻头发酸。
赵玦不疾不徐道:“嗷呜,安静。”
嗷呜的低狺如遭剪子铰断,即刻没了。
原婉然睁大眼睛,嗷呜顺从赵玦但并无惧怕之情,也就是说,它之所以静下来全是单纯服从赵玦命令?
赵玦看穿她疑惑,道:“家中大狗全听我号令,嗷呜亦然。”
大狗牙尖力大,足以杀人,他防患未然,让别业里所有大狗受调教,从小便识得并服从自己这个家主,杜绝安全隐忧。
原婉然闻言恶心晕眩。
她耗尽气力出逃,不但自始至终深陷在赵玦布下的天罗地网,竟连嗷呜也逃不出他的手掌心。
她一时立不稳,身形摇晃。
赵玦不假思索上前欲待扶人,原婉然一见他靠近,慌忙后退。
赵玦面色微变,随即恢复常态停住脚,不着痕迹收回手。
原婉然出逃失败,所受打击非轻,初时失意恍惚,如今渐渐回神,便想立时弄明白一桩事。
“你如何知道我要逃?”
“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为。”
“究竟哪里教你起疑?”
赵玦见她执意做个明白鬼,便道:“你不轻易谈旁人私事,却自行向池娘子祝愿她回乡,夫妻团聚。举止反常,必有异动。”
原婉然大吃一惊,胸口窒闷恶心更甚:“你连池娘子和我往来都在刺探?”
“不错,”赵玦索性打开天窗说亮话,“在你利用风筝挟带字条之后。”
原婉然面上本就不剩多少血色,这下苍白如纸:“原来你知道……那么风筝……”
“已经全数找回。”
原婉然料不到赵玦对她掌控严密至此,这已非对她兜头撒下天罗地网,竟是活埋,将她困得密不透风,一根指头都动不得。
她看向赵玦,无法掩饰忌惮怨愤。
赵玦亦早已满腔怒气,终究不愿当着手下的面向原婉然发作,教她没脸;再见她气色越来越差,天大的火气也不得不稍作退让。
他说:“你已经折腾一宿,先回流霞榭再说。”
他心绪不悦,口吻不免冷硬,要说恶意其实没有。
只是原婉然想到赵玦往日拆散她们夫妻,又冷眼旁观自己在园里白白奔忙一夜,听在耳里便觉是猎人戏耍猎物一通之后,还要指挥奚落。
“我不回去!”她喊道,回身便往园外跑。
相离原婉然最近的亲随猱身上前要拉人,赵玦喝道:“不准碰她!”
他辞色罕见严峻,那亲随忙不迭退开。
园门外是条长巷,原婉然跑到巷子尽头,发现那处的角门已经关上落锁。
“我要出去!”她下死劲掰扯铜锁,自然掰不动,便拍打角门,继而拳打,“放我出去!”
她明白自己在做蠢事,纵使敲烂拳头,喊破喉咙,门不会开,更不会有人纵放自己。她的卖力反抗徒劳无功,反而可能更加激怒赵玦。
当务之急该向赵玦求告服软,哪怕虚情假意,屈膝献媚都在所不惜,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
可是她受不住了。
赵野疯了,她必须回家。今夜是她仅剩的逃离机会,仍旧化为乌有,和从前几次一样,以为见到一线曙光,到头来电光幻影。
她连言谈举动都逃不过赵玦眼睛。
想到此处,她的肉身明明在呼吸,却窒塞得提不上气。
很久以前她听赵野说过一种叫“贴加官”的刑罚,以湿透的桑皮纸一张张覆在犯人脸上,教人无法呼吸,窒息而亡。
她正在受刑,她在赵家便是受刑,就要闷死了。
如果继续一声不吭,屈从赵玦摆布,真的要闷死了。
她拍门呼喊,将种种焦灼灰心都撒在这道出不去的门上。
一道力量攫住她的手,将人由门后拉开。
原婉然回神一看,拉她的人是赵玦。
“别做无用功。”赵玦说。
原婉然恨恨瞪视这个阻挠她海阔天空的人,赵玦却不看她。
他牢牢抓住原婉然双手端相,就着火光不曾发现皮肉伤,依然吩咐一旁亲随:“让大夫去流霞榭候着。”
他恐怕原婉然今晚受伤,提早让家中伤科大夫彻夜侯命。
“呜……呜……”嗷呜在原婉然裙畔急得团团转。
它察觉主人心绪激动,却不明所以,无计可施。
“嗷呜别动。”赵玦下令,并唤来亲随,“将狗带走。”
那亲随依令抱走嗷呜,当嗷呜醒过味自己教人从原婉然身旁远远带开,已经受制于人跑不了,只能吠叫。
“嗷呜!”原婉然想奔过去夺回狗,却教赵玦拉住,带往流霞榭。
“放开我!”原婉然试图挣脱。
她累了一晚,若是逃出赵家,精神振奋之余不难激发力量,一鼓作气赶路,可惜事与愿违。为着功亏一篑,她灰心丧气,体力跟着渐渐不济,嗓子都有些哑了。
赵玦听出原婉然声音不对,恰好经过厨房,便将她带进里头。
那厨房连带柴房一排几间房子,一间辟成茶房,专侯主子在周遭游玩休憩,为其供应茶食,其余房间管附近粗使下人饭食。到了夜里,有下人在此上夜。
赵玦支开在此夜看守的婆子,严令她不准对今晚之事多言。
他在茶房挑了最洁净的茶碗,倒茶递给原婉然:“喝口水润润嗓子,有话回流霞榭再说。你生气,就砸流霞榭出气;砸不够,换地方再砸。”
原婉然不曾伸手接茶,今晚两人原形毕露,以本心相见,赵玦应付裕如,优雅自若,更衬出自己满盘皆输,任人宰割的狼狈困窘。
她心绪灰凉,一时不管不顾,道:“我要回家。”
铿锵一声,赵玦重重放下茶碗,强抑的怒火腾地窜起。
他剜视眼前女子,但见她满面固执,端的油盐不进,捂都捂不热。
然而下一瞬,那女子倔强气恼的双眸涌现水光,须臾水光碎裂,化作泪珠落下。
明明只是两行水液,只是他人的水液由他人眼里滑落,划过他人肌肤,赵玦却错觉那是把钢刀,不偏不倚扎进自己胸膛乱搅,割裂五脏六腑。
他一团盛气因此再度消减:“这儿就是你家。”
“不是!”
“就是,”赵玦火气又上来了,“除了这儿,你不能再有别的家!”
原婉然对赵玦的专横反感极了:“哪儿是我的家该由我说了算,不归你管。我说这儿不是我家就不是我的家,我的家会有……”她话到嘴边慌忙将两个丈夫的名字咽回肚里。
不能在这风头火势的当儿向赵玦提起韩一和赵野,不能教他想起他们找麻烦。
其实何须她说出整话?赵玦已然会意。
“又是韩一和赵野,又是那两匹夫!”他抓住原婉然双臂摇撼,“你为什么总想着他们?你要惦记他们到何时?”
原婉然前时求援,今夜又出逃,教他火气一重积一重,积怒深重,不过苦苦压抑。如今几乎听到她亲口证实对丈夫念念不忘,妒意伴随怒意迸发,变本加厉燎红了他的双眸。
他盛怒之下,手劲过大,原婉然吃疼,只是咬紧牙关不肯求饶。
因此赵玦不察,狞笑道:“你的家一定要有那两匹夫才算数吗?行,我取来他们脑袋,送你当球踢!”
他目睹原婉然因为自己放话威胁而大惊失色,在那之前,她不声不响,身子却不由自主瑟缩。
他立时警觉自己手重,弄疼她了。
赵玦清醒了。
世上只有一个小村姑,纵使经历过千千万万年,来来去去千千万万人,都只会有这一个她,一旦没了,就永远没了。
他加诸于原婉然臂上,铁箍一般的十指立刻松缓。
原婉然也清醒了。
赵玦扬言杀害韩一兄弟,他说这话再无惯常沉稳,俊美绝伦的容颜出现前所未见的狰狞,比起虐杀西山劫匪那时,远远来得阴鸷暴戾。
他要动真格,下杀手了!
原婉然浑身发抖,顾不得臂上生疼,凑近赵玦拉住他衣衫。
“你别害他们,求求你,都怪我不好,我错了,不该逃跑,不该惹你生气,这里是我的家,我不走了,我没有别的家,只有这个家,我这就回流霞榭。”
她方才多倔强,现今便多卑微,眨眼间姿态判若两人全是为了韩一和赵野。这般委屈求全适得其反,再度激怒赵玦。
他抓住原婉然扯住他衣衫的手,咬牙道:“那两匹夫究竟有什么好,我哪里比……”话到半途煞住了。
他不肯自轻自贱,拿自己和两个匹夫相提并论,更不能让原婉然识破他不欲告人的秘密。
向无意于你的人示爱,不过是枉然示弱;对与你水火不容的人示爱,更是自取其辱。
他再沦落,再能放低身段,天潢贵胄与生俱来的骄傲终究不许他这么做。
原婉然早经木拉说破内情,在赵玦跟前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情愿装糊涂,方才听他言语间似要挑明这个秘密,她惶恐极了。
一旦赵玦捅破这层窗户纸,两人会是何等光景,该如何收拾?
她来不及遮掩,畏惧心绪已自浮上脸面。
赵玦目光始终不离原婉然,因此乍一眼便懂了:她知觉了。
她知觉了他的心思,神色如见蛇蝎,避之唯恐不及。
果然如此……赵玦自嘲一笑,果然是自取其辱。
他刹那心冷,不由分说将原婉然拉出茶房,推入最边间的柴房。
“你既看不上流霞榭,就待这儿,正好和你那破宅子相仿。”
原婉然受了推抢踉跄进房,待得立稳回身,房门已关上,还教人拿了什么物事当啷穿过门环,让门后的她推不开。
“取门锁锁住,”门外赵玦吩咐亲随,“不准下人接近此处。”
原婉然扑向房门,喊道:“玦二爷!”
彼时天色渐亮,但柴房窗小,光线幽暗,她看不清地面起伏,踩在上头一个趔趄,啊了一声,险些摔倒。
赵玦转身欲走,听她惊呼,身形一滞。
不多时门后传来原婉然话声:“求求你。”
赵玦停下脚步,竖耳倾听。
“求求你,别动韩一和赵野!”原婉然央求。
赵玦铁青了脸,闭上双眸深吸一口气,随后睁开眼,快步离去。
原婉然在门后哀求,门外有人道:“原娘子,你求也无用,二爷已经走了。说不得,请你暂时委屈一下,等二爷消气,自然放你出去。”
那是赵玦的亲随之一,他边说边将门上锁,完了事,告了罪也走了。
门外人走光了,原婉然也实在累了,她环顾房里,四面墙下木柴垒得小山一般高,其中一角搁了茅草堆,生火时节拿来引火用的。
她将茅草堆当成垫子坐下,一边静静淌泪一边思索如何停息今日祸事。
不知过了多久,屋里闹起吱吱叫声。
原婉然抬眼一瞧,几只老鼠从她前方掠过,争先恐后要夺门而出,却教锁上的门阻了出路。
那群老鼠开始横冲直撞疯跑,原婉然正觉不祥,地面晃动了。
起先微晃,很快震动加剧,柴堆上方木柴笃笃互撞。
地动了!原婉然跳起来,冲向门后,喊道:“快来人,开门啊!”
地动厉害,十来步的路程她都走不稳,屋外也无人回应她的呼救。
她拼命拉扯门扉,无奈不过枉费工夫。这同时,头上窸窸窣窣作响,落下一蓬蓬尘埃,她捂鼻咳嗽,抬头看去,正好一片黑影当头落下。
她慌忙后退,说时迟,那时快,锵的一片屋瓦砸了下来。
这只是开端,柴房屋瓦开始叁叁两两落地,原婉然闪闪躲躲,避到了墙下柴堆前。
她不错眼地紧盯屋顶,躲避落瓦,忽然几道天光由屋顶透进来——屋顶由彼端起始,朝她这儿成片成片松动,即将坍塌。
原婉然逃无可逃,只能紧靠柴堆蹲下,抱头缩成一团。
下一刻,屋瓦抑或木柴落了下来,砸在她身上,包括头顶。
她一阵疼痛昏眩,不支倒下。
陷入全然的黑暗以前,原婉然脑海模模糊糊闪过一个念头。
相公,我想回家……
另一头,赵玦走在回到退思斋的路上,神态沉静,不过胸膛起伏急促,步伐过于迅速,失去平日的闲适自在。
他吩咐赵忠:“备车,我要去商号。”
“二爷,你整宿未眠……”
“事不等人。”
“生意要紧,二爷也要保重身子。”
“大事将了,往后有的是闲工夫保重。”赵玦说着,缓下脚步。
他自觉脚下不稳,好似身在行舟,头晕目眩,疑心自己又将发病。
身旁竹林给了他另一个答案。
林间丛丛修竹摇颤,竹叶簌簌抖动。
地动!赵玦恍然大悟,脱口道:“小村姑!”转身折返,朝来路疾奔。
跑了几步,他忽感虚弱,身上发软脱力,紧接着眼前暗下,从此人事不知。
_φ(-w-`_)_φ(-w-`_)作者留言分隔线_φ(-w-`_)_φ(-w-`_)
那个……下一章更新估计要延迟几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