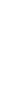赵玦说的每一个字池敏都听得清楚,却是作梦都料想不到他有此话。
“回家?”她以为自己听错了。
“是,水路脚程快,再者当年你走水路来京,不曾晕船,故此选择水路。”
赵玦将话说到这般明白,池敏意会他当真要将自己送走。
这日她因为地动之故,教赵玦挪来别庄,遂问道:“玦二爷,这回灾情竟然这般严重,必须避走数百里之外?”
“此事与地动有关连,但和灾情干系不大。”
“玦二爷言下之意是?”
“这回地动,京城远近多有死伤,不分男女老少,猝不及防,一夕丧生。我寻思祸福难料,人生苦短,不应蹉跎光阴。比如池娘子,一直思量重归家乡。”
“我……”
我已经不想回去了,池敏忖道。
许家在家乡声名狼藉,和它沾亲带故便要遭殃,那许八郎还另娶妻房。——哪怕他不曾另娶,她也……
无奈她人前长久表态思念家乡故人,不好乍然改腔,遂有口难言。
赵玦温声道:“赵某并无他意,羁鸟恋旧林,池鱼思故渊,人之常情,况且池娘子重情义,方才念旧。”
他言语间抬高池敏,更教池敏想不出借口推拒。
赵玦又道:“是以赵某寻思期间让池娘子返乡瞧瞧,缓解思乡之情。”
池敏登时松口气,原来赵玦只是让自己回乡一游。
须臾她又狐疑,从前自己想家,赵玦都不曾放人,这回他改弦易辙,真个因为地动有所感悟,抑或有了原婉然,便将自己看得可有可无?
不对,旋即她宽解自己,赵玦只送自己来别庄,却将原婉然丢在需要修缮的赵家别业。
然则人心易变,万一她回乡以后,赵玦改了心肠,将她丢下不理,她和奶娘如何是好?
池敏心有疑虑,迟迟不言语。
赵玦问道:“池娘子可是觉得赵某安排有不妥之处,碍于情面难以启齿?”
池敏无法坦言自己疑心,遂强笑道:“我只是想起从前玦二爷说,待八郎赎身从良,且能自力更生,就送我返乡,不意此事能提前。”
赵玦当初返乡旧话是任凭她一去不返,和这次让她去去便回是两回事,池敏故意将两事相提并论,混为一谈。
她盘算若果赵玦在乎她去留,自会言明并无放人意思,她亦得以宽心。
却听赵玦道:“如若池娘子愿意从此长留家乡,亦无不可。”
池敏犹如一脚踩空,大吃一惊:“玦二爷?”
赵玦温声道:“池娘子来京数年,一向难得开颜,终是京城风土人情不合你脾胃。”
“我……”池敏连忙道,“我乍来京城,确实曾经水土不服,长住久居倒渐渐惯了。此地和我家乡多所不同,不过自有它的好处。”
赵玦温和如故:“只是池娘子思乡之情从来有增无减,足见在你心中,梁园虽好,终非久恋之家。”
“这……”
池敏越听越惊,赵玦原本只说送她回乡一游,何以自己假意试探,他竟顺水推舟?
岂难道她弄巧成拙,玩弄心机教赵玦厌烦,索性撒手?
池敏正自猜疑,赵玦走到案前,由案上拜匣取出一只信封,走回递向池敏。
“设若池娘子回归故里,你我相识一场,赵某有些小微物相赠。”
池敏愣愣问道:“玦二爷,这是?”
“通州一处宅院地契,供池娘子栖身。虽是浅房浅屋,倒还堪可居住。”
池敏听说,身子冷了半边。
赵玦早将地契备在手边,看来早早便存心将她远远打发。她方才试探,竟是撞进他挖的坑里,遂了他心意。
但是几时赵玦变了心?这一向她待赵玦淡淡的,他都不以为意,恒常礼遇,岂难道积怨至今,终于忍无可忍?抑或他有了原婉然,喜新厌旧,可又为何将原婉然丢在别业不理?
她心乱如麻,到底要强,勉定心神道:“玦二爷,无功不受禄。况且我家乡在永州,回的也是永州。”
赵玦道:“许家在永州不受待见,池娘子教人发现回乡,恐怕要受牵连。不如移居通州,通州邻近永州,水土风俗相仿,容易习惯。池娘子闲时思乡便回永州走走,两地路程近,路上平靖,旅途安全。”
他由信封抽出一张字纸递去:“请池娘子展读。”
池敏聆听赵玦剖析居处利害,意识自己日后孤身立足世间,举步维艰,登时没了主意,怔怔接过字纸。
纸上满篇文字,她强自专注心神从头读起:“立买卖人段十一郎有祖上宅院一所,门面叁间,到底五进,花园一段,田地五百亩……”
池敏又吃一惊,五进宅院带花园,另有五百亩田地,这哪里是浅房浅屋?
她不由细看下去,赫然发现契约中将买方写上她的名姓,纸上盖了官章红印。
这纸地契经过官府盖章验明,依大夏律法,她是田庄唯一正主,旁人不能染指,出钱赠契的赵玦不能,即使许八郎仍是她丈夫,都不能擅自作主。
落款载明了立契年月日,这行文字更教她讶异。
池敏问道:“玦二爷,许家出事之后,你将我带来京城之前,便买下这座田庄?”
“是,我思量许八郎没准真能接你还乡,许家家业却未必能恢复如初。许八郎一个男子吃苦无妨,不能委屈池娘子。”
池敏红了脸,她猜疑赵玦不怀好意,喜新厌旧,其实人家数年前设想到她将与前夫破镜重圆,照样代为谋划后路。
“我说过,无功不受禄。”她说。
赵玦有他的气度,她也得有她的风骨。
赵玦道:“池娘子切莫推辞,我并无他意,不过爱惜你才华,不愿你那一手好字好画教柴米油盐拖累埋没。”
池敏闻言,想到奶娘江嬷嬷往日叨念赵玦这等夫婿白日打着灯笼都难找。
此时此刻她深以为然,上哪儿再找这么一个人,年轻有为,貌如仙人,数年如一日温存体贴,珍惜她的才情?
池敏想到此处,心口发热:“若我不愿回乡呢?”
“池娘子?”
“玦二爷消息灵通,应当听说许八郎再娶了。”
赵玦默然,随后道:“赵某生怕池娘子难过,不曾告知。事关许家家务,外人亦不好多嘴插手。”
“我不难过,我……”池敏决意一搏,遂道,“他已变心,我亦如此。我心悦你。”
“池娘子,”赵玦温声道,“你一时激动……”
“并非一时激动,”池敏道出心意如释重负,其余心里话随之淌出舌尖,“更非许八郎另娶,我才回心转意。早在此前,我便……只是你始终不曾将话挑明,我身为女子,岂可自轻自贱,自行俯就?”
她忘了何时起,眼里虽然不见赵玦,心中却生出他的影子,朝朝夕夕影影绰绰。他的到来逐渐成为她日常的盼头,可这分情感无法言说,她在赵家暧昧不明的身份,她从小受的礼教都不容许她表态。
她只能拒他于千里之外,等待他下回接近,在她又将他推开之前,抓紧两人仅剩咫尺距离的瞬间,不为人知地尽情感受他释出的那点情热。
池敏说完话便低头不敢正视赵玦,面庞火烧火燎,一颗心跳得呼吸都急了。
不多时,她听到赵玦回应,话声一如往常温雅平稳。
“我头一回见到池娘子,是在许家花园,你和许八郎邀了诗友在园里赋诗取乐。”
池敏听他在这当儿提及前夫,心中不安。
赵玦道:“当日不少女眷与会,赵某第一眼便留心于池娘子。姿貌纤丽,气质清洁,好似水晶人儿。”
池敏听说心上人当年对自己注目留心,又羞又喜。
赵玦又道:“池娘子才思敏捷,诗画俱佳,在我所知女子中,才情数一数二。”
池敏受了称赞,心中更喜。
赵玦又道:“那日赵某记忆犹新,你和许八郎联诗,诗成,夫妻相视一笑,恩爱之情溢于言表。你言行庄重,唯独笑向许八郎时候,神气娇柔,看来十分倾心于他。”
池敏听他又提前夫,再度不安。
赵玦道:“自那日起,我便期待今日到来。”
池敏心脏重重一跳,赵玦头一回见到她便期待她移情别恋。
她满怀热望抬起头,和赵玦四目相对,岂知那位谪仙般的男子面上也无悲喜也无情,沉静如深水。
“今日再一次印证我主张:世上没有情比金坚这回事。恩爱夫妻之所以能是恩爱夫妻,无非遇上的诱惑不够大,磨难不够重。”
“玦二爷?”池敏无措轻唤。
赵玦淡淡道:“池娘子,京城乃是非之地,不宜久留。”
“玦二爷,你什么意思?”
“池娘子是聪明人,用不着赵某明说。”
池敏确实聪明,然而短短一番交谈历经几番转折,将她打懵了。
赵玦因说道:“赵某立意让彼此情面上过得去,好聚好散,可惜事与愿违。”
“好聚好散”,池敏听得这四字,顾不得礼数细细打量赵玦,终于瞧出来了。
这人言谈举止尽管温和有礼,无非教养使然,从前的暖意再不复见。
他对自己已然无所留恋。
池敏明知多言无益,到底忍不住究问:“你从何时变了心意?”
赵玦沉默以对,投向她的目光不曾动用任何一种感情。
池敏警悟事实比她设想的更难堪,话都说不完整了:“你……可曾……”
“不曾。”赵玦答得迅速而果决。
池敏白着脸道:“你从头到尾将我当成乐子戏耍。”
“赵某只需要幌子。”赵玦说。
他在人群中第一眼便留意池敏,不为别的,池敏肖似德妃,出身小户诗礼人家,才貌双全,模样柔弱清净。
碰巧许家获罪抄家籍没,女眷即将沦为女乐,他不惜放下商号公务,在永州盘桓数月,动用多方人情和大笔银钱,打通重重关节将池敏赎免,带回京城。
池敏本人并不值得他费这许多工夫,但利用她摆出大阵仗作态,取信于德妃这事值得。
他要利用池敏降低德妃对他的防心。
赵玦不曾懂过德妃,王府覆灭之后,倒是懂得了。
德妃不会相信有人愿意仅凭情份便不计利害护佑托举他人,若是出于私利私欲,有所图谋,她方能理解,因为她自己便是那样的人。
一旦她能理解,便会相信。
赵玦需要德妃相信自己并无反叛之虞,从而卸下防备,放出更大权柄给自己。
那么有什么比按照德妃的模样找个心上人,更能教她误信自己孺慕生母到了反常执迷的地步,因此只有任凭她摆布的份呢?
德妃以为儿子对自己怀抱阴暗扭曲的情欲,自然要恶心,正如她错认儿子弑父,见子如见邪祟。
然而与此同时,她也会沾沾自喜,并且确信儿子既然甘为自己一再冒天下之大不韪,对自己当真死心塌地,绝无可能脱离掌握了。
池敏的存在还让德妃自以为手中多添一个把柄,能用来拿捏要胁儿子。
让德妃自认立于不败之地,他便有更多空子可钻。
这节赵玦无意向池敏解释,池敏也无心追究,她厉声质问:“赵玦,你这般耍弄人,不亏心吗?”
“不,”赵玦斩钉截铁答道,“你也绝不以为进教坊比进赵家好。”
池敏语塞,赵玦拿她作戏,此事固然令人羞愤,然而确实好过堕落风尘。
她搜索枯肠,只剩一事能对赵玦还以颜色:“所以你真正心爱的,是原娘子?可惜落花有意,流水无情。”
“原娘子……”赵玦话声不觉柔了,“她仙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