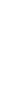五日后,苏权请了张松来家是饮宴。张松早期经商起家,家底丰足后,花钱托人转了农户,现在也是小有产业,虽然子女仍不得科考,但平时以乡绅富户自居,也无人攀咬。只不过张家毕竟是小户,与苏家一比便低了一层。此番到苏家来,张松尽力作出一副淡定闲适的模样,只怕被人看轻了去。
拜见过苏权父母之后,张松便被妹婿引着来到后院一处偏厅。苏家后院颇大,其中又种了不少花树,此时五月中旬,正是枝繁叶茂,故而苏权令人将酒席摆在院中偏厅之内,喝酒赏景、自在逍遥。
两人相携落坐,张秀过来说已经准备好宴席,这就命人上菜,说完之后也不去看哥哥,扭头要走,却被苏权一把拉住手,说:“舅兄好不容易来一趟,你怎的还要走呢?快些过来坐下,今日又没外人,我们一家正好同吃同乐,叙叙别情才好。”张松闻言点头称是,一起请张秀入席,三人分别坐定,仔细端详了妹妹两眼,便对苏权说:“见她面色红润,就知日子过的自在,早就说她是个命好的,遇到伯安真心待她,也是她的福份。”
“舅兄这样说便是见外了!”苏权拿起酒壶为张松斟酒,又给自己倒了一杯,说:“秀儿既是我的妻子,便是一家人。况且这一年来,她为了家中事务日日操劳,教养子女尽心尽力,硬说起来还是我占了便宜。此番请舅兄前来,先要谢过舅兄将如此贤妻嫁于我家,苏权先干为敬!”说完一饮而尽,见张松也将酒喝净,又倒了两杯。张秀怕他喝多难受,拉着苏权的袖子说:“今日我特意命人做了好一桌酒席,不想竟是无人问津,实在委屈得紧,求你二人先尝尝味道如何也好啊!”苏权闻言握住她拉着自己袖子的手,看着张松笑了笑,说:“看来是我莽撞了,舅兄也来尝尝我家的厨子手艺如何!”
然后便是推杯换盏吃吃喝喝,席间张秀吃的甚少,不去看自己哥哥,也不同他搭话,只是偶尔劝苏权少喝些,苏权口中应着,却依然不断劝酒,张松也是来者不拒,皆是一饮而尽。突然丫环进来报白家派人来请,说是有事相商,苏权起身向张松告了声罪,又叫张秀留下陪他,便自去了。出门时看了那丫环一眼,那丫环点点头,也退下了。
10、第十章 露马脚兄妹受难
瞧着苏权走得匆忙,张松突然福至心灵的想:这可是个大好的机会!回头看见妹妹只是端坐在桌旁,正垂头绞动手中的帕子,胸前一对奶乳被两条手臂拥挤着,随她手上的动作微微摇颤,映着她身上的艾绿色锦锻襦裙,好似一湖春水般漾花了张松的眼。不过想到苏权刚走,此时怕是还没出得苏府大门,只得生生忍下,无意识地舔了舔干渴的嘴唇,对张秀说:“秀儿这些日子过得可好?”
“还好。”张秀仍旧是不抬头,见她只是答了两个字就不再出声,张松心中暗暗发笑:这妮子竟然同着我也害羞起来,可见是长大了。视线不由自主地又滑向妹妹胸乳,心中更加肯定:的确是长大了……
张松这边对着妹妹愣神,张秀却是坐立不安,哥哥的眼神仿佛带着温度,看得她浑身发热。曾经她是万分喜欢的,只是现在不同了,若是在这里闹出什么事情来,自己一辈了就毁了,决不能坐以待毙。于是想了想,说:“哥哥可是饱了?”
“饱了饱了!”其实他也不知道自己是不是饱了,只不过身上有一处更饿,已经顾不得肠胃了。
张秀起身从张松另一边绕过桌子走到门前对他说:“既是饱了,那便起来溜溜吧,食后不宜久坐,不如我们去院中凉亭里说话可好,省得这里闷热。”说完扬声呼唤下人,可是叫了几声也不见有人前来,莫名地感到不妙,赶紧说道:“这人都跑到哪里去了,定是看到夫君不在,全去躲懒了。哥哥稍坐片刻,我去寻个人来!”边说边往门外走,马上就到门口了,却眼睁睁看着那两扇门被人关上,而关门的,正是自己的哥哥!”
“你我兄妹好久不见,妹妹这番作派可是太过冷淡了,反正此处无人看候,不如你我好好聊聊?”张松整个人靠在门上,令张秀无路可逃,见妹妹出落的比一年之前更加勾人,更是淫意难忍,低头一看,果然胯下衣襟已经被顶了起来。
不只他自己看得到,张秀自然也看得到,心中预感更加不妙,稍稍后退了两步,义正词确严地说:“哥哥喝醉了,不如让我出去,找个丫环来伺候哥哥稍事休息罢?”
“如此甚好,你快去罢!”张松侧身让到门边,直勾勾地盯着她,说:“妹妹快去,我在这里等着!”
张秀仔细估算了一下,若是自己动作快些,他应当是抓不到自己的,于是点点头,快步朝门口走去,手刚摸到门上,就觉腰间一紧,接着就是一番天旋地转,等回过神来时,发现已经被哥哥压在地上了。哥哥那肉棒正顶在自己小腹之上,张秀生怕他真的做出那事来,却也不敢高声叫嚷,就算是被下人看到,也是说不清楚的,哪怕是亲生哥哥,男女七岁不同席,这般情形也是见不得光的。张秀越想越急,却死活挣脱不开哥哥的钳制,直到急出了眼泪,哭着说:“哥哥是要逼死我么?这样子若是被人看了去,妹妹便只能自尽了!”
“怕得什么!”毕竟是自己养大的妹妹,方才有意躲闪虽然让人气愤,但此时一哭,张松又觉得心软了,低头亲吻她的泪珠,含糊道:“他若是真敢休了你,我便把你接回家去,以后我们日日做夫妻,夜夜进洞房,岂不是更加快活?”
“哥哥醉的厉害,已经不知我是谁了,求你快些放开我罢!”张秀手里握着刚刚偷拔下来的梅花簪,到底还是不忍伤他,哭着求了又求。但张松已然精虫上脑,早没了人伦之念,一把抓住妹妹的一只奶乳揉捏起来。心知他已经铁了心定要得手方肯罢休,一时间又惊又怒,抬手便将那梅花簪狠狠地插入哥哥肩头,张松哀嚎一声爬起来,怒气冲冲地问她:“你这是做什么?疯了不成?”
“你还好意思问我?”张秀狼狈地爬起来,泪珠断线一般的往下滴落,嘴角上却是挂着笑,恨自己当初不懂事,又笑自己天真痴傻,又哭又笑地说:“事到如今,你还好意思问我做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