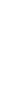“出什么事了?”
林秀梅看到他脸上的表情,心底升腾起非常不好的预感。
安静的夜里,王乃器凝重地看着她,半响才沉声说:
“影子!”
“他是谁?”
“徐佑正,边区保卫部副部长。”
“不可能!”林秀梅勃然色变,反驳的话脱口而出,或许是太过于震惊激动,啪一声,手中的剪刀掉在了地上她都不自知。
她就是从宝塔山过来的,不但在鲁艺培训过,还参加过保卫处第一期侦查情报干部特训班。
徐佑正不仅仅是他的上级,还是她的教官和老师,这样履历辉煌兢兢业业的老资格党员怎么可能是内奸,是军统打入内部的走狗。
“沉住气。”
王乃器低声呵斥着,小心翼翼将地上的剪刀捡起来,严肃道:
“没什么不可能,人都是会变的,况且这是美人鱼发来的情报,他的情报从来没出过错。”
“可是.”林秀梅嗫嚅着,不知如何反驳。
“可是什么?”
“这里面一定有误会,老徐是老资格的地下党,为党鞠躬尽瘁,我们不能因为一个藏头露尾的不知身份的美人鱼就怀疑自己的同志…
你说人都会变的,美人鱼呢?你怎么证明美人鱼没有变质,你怎么证明这不是他和军统谋划的阴谋诡计?”
“你少给我提什么老资格的地下党!”
王乃器也被她这态度和语气激怒了,尤其她还怀疑美人鱼,他低声喝道:
“张某焘还参加过一大呢,他比首长的资格都老,可他现在呢?还不是背叛了党,背叛了人民,成了军统的走狗!”
“这”林秀梅被他严肃的神色吓住了,喘着气,顿了顿,有些艰难地说:
“可我还是不能接受这个事实。”
“我理解,我也觉得不可置信,但一个合格的情报人员绝不能意气用气,应该有冷静的研判能力。
我们的职责是传递情报,而不是否决情报。你可以怀疑质疑,但要相信组织,组织会核实清楚的。
事情在没有验证之前,个人不易发表看法,更不能对我们打入敌人内部的同志无端怀疑!”
林秀梅努力控制着自己的情绪,点了点头,有些艰难地问:
“还有什么?”
王乃器的神情依旧严肃:“沈之岳也就是沈辉,已回归军统,化名孙子超,出任谍参科科长。
现在可以证明就是他向军统出卖了新四军的情报,他是第一任影子,这个徐佑正是他的接替者。”
“沈辉?!”林秀梅的眼神一滞,这个人她也认识。
二三十岁的样子,气质冷静沉稳,连续几年的模范党员,她还听过他慷慨激昂的讲话。
想不到他也是敌人打入组织内部的内奸,这.还有什么可以相信的,今晚收到的情报严重冲击着她的认知和价值观,让她头皮发麻,大脑一片昏沉。
“情报工作就是这样,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王乃器叹息一声,又说:“还有件事。”
林秀梅猛地抬起头,脸色越来越差,她不敢相信也不愿再听到宝塔山还潜伏着敌人的卧底,她觉得自己的心脏受到的冲击已经够多了,不想再听到不好的消息。
“那29名牺牲的同志里面,有一个叫乔玉坤的是军统的替死鬼,不是我们的同志。”
“军统的人?”
“对,戴春风心狠手辣,连自己人都不放过。”
“他这么做是为了什么呢?让乔玉坤伺机打入我们被捕的同志中间,获取信任收集情报,还是对他们自己人的试探?”林秀梅皱着眉头,望了望王乃器,又说:
“执行处决任务的是杨进兴和张义,戴春风是在测试这两个人吗?”
王乃器看着她,心里一下就明白了,但还是问:
“你想说什么?”
“我们打入敌人内部的同志提供的情报说,望龙门看守所之前关了军统局的几个处长级人物,龚仙方、沈西山、魏大明、张义。
随后这几人又被突然释放,现在戴春风又用这样的方式测试杨进兴和张义,他针对的是谁,还不够明显吗?”
顿了顿,她狐疑地看着王乃器:
“老王,你说实话,这个美人鱼到底是不是张义?你到底知不知道他的真实身份?还是你刻意在隐瞒什么?”
王乃器一愣,表情丝毫看不出真伪:
“我也不知道。”
见她一脸不信,他又补充说:“知道他是谁重要吗?”
“当然重要,我们需要甄别清楚,他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我只知道他是我们的人,自己人,中国人,这就够了。”
王乃器深深望着他,严肃道:“是谁不重要,只要他知道自己是什么人,记得心里的任务使命就够了,身份反而是他的羁绊,就算我们猜到了,也要当做不知道,这是对他的保护。”
说话间,他严肃的表情里,带着几分景仰,那是对这位潜伏在敌人心脏中同志的崇敬之情。
接着,他长叹一声,结束了这个话题,说:
“现在要做的就是将情报汇报给上级,让组织研判分析。”
一听这话,林秀梅瞬间回过神来,拿起床头的一件衣披上就要出门。
“你干什么去?”王乃器连忙将她摁住。
“我去送情报。”
“哪有新婚之夜新娘子出门的?”
王乃器劝慰着,“再说了,办事处明里暗里都有军统的特务盯着,你现在可不是公开身份,一旦被他们看见,身份肯定暴露。”
“可”
“可什么?我说了遇事要冷静,越是危机时刻,越不能乱了阵脚,着急、愤怒、冲动,只会犯下幼稚的错误,让敌人抓住破绽,一切按照流程来。”
“可是影子就潜伏在我们内脏之中,我能不着急吗?”
“他又没长翅膀,还能飞了不成?”王乃器信心满满,“要相信组织,如果他真有问题,就跑不了。”
“好吧。”林秀梅长舒一口气,无奈地耸耸肩,又不服气地仰头看着他:
“还有什么要交代的?”
“这回美人鱼传递的情报署的是深海的代号。
我懂他的意思,从今天开始,我们就当美人鱼不存在,用深海的代号,这样可以让敌人摸不着头脑,另外.”他思忖着,顿了顿,又叮嘱:
“你给上面汇报的时候要说明这一点,或许我们可以联合老家的首长演一出戏。”
“你是说兵不厌诈?”
林秀梅挑眉看着他,看着这个貌不惊人的“丈夫”,论眼界和水平,还是这位老地工想的更远更深,不由佩服起来。
“你想怎么做?”
“这个徐佑正隐藏如此之深,老奸巨猾,自然非等闲之辈。
他所在的部门又如此重要,老家有任何风吹草动,怕是逃不过他的眼睛。
不妨将计就计,直接告诉他在军统潜伏着一位叫深海的同志,等他成功送出情报,我们再一举将其拿下,将他的同党一网打尽,你说戴春风会怎么样?”
“疑神疑鬼!先是美人鱼,现在又冒出个深海,戴春风怕是彻底睡不着觉了,看谁都是卧底内奸,他查还是不查?只要查,必然人心动荡.”
林秀梅展眉一笑,对老王更加佩服了,都说家有一老,如有一宝,此言诚不欺人。
想了想,她建议说:“或许可以让老家给深海杜撰一份详尽的资料,把他的入党资格提前一些,就说他是32年就奉命打入军统特务处时期的卧底,这批人如今可都是军统的高层。”
“这是给姓戴的心里扎老刺啊,非要了他的老命不可,蓦然回首,身边还有可以信任的人吗?”王乃器笑了,拍板说:
“就这样向上面建议。”
说完这话,他才发现林秀梅异样地望着自己,不由一愣,笑着摸了摸自己的下巴,开起了玩笑:
“怎么,才发现咱老王的魅力?”
林秀梅哑然失笑,沉默了一会,服气地说:
“我现在才明白理论和现实的差距,培训班上学得再好,不实际体验一遭,根本不明白这份工作的复杂和惊心动魄。”
王乃器闻言愣了愣,看了看他,什么话都没说。
心里感叹着,是啊,是够复杂的,就像地下的暗流,静谧、曲折、湍急、甚至凶险。
不过,这些让人精神为之一紧的词,表面上绝对不能显露半分。
当然了,这些经验总结,都是无数牺牲的同志用血和泪的代价换来的。
“好了,睡觉吧。”
收敛好情绪,王乃器摆摆手,将灯盏吹灭,合衣躺到了床上。
林秀梅也重新躺回了床上。
黑暗中,两人都睁着眼睛,今晚经历了这么大的冲击,更睡不着觉了。
一夜无眠。
天还是鱼肚白时,只听“咯吱”一声,王乃器家的木门被打开了。
王太太林秀梅挎着一个菜篮子从里面走了出来,她反身将门带上,走了。
一个扫地的嬢嬢看着她,打趣道:
“王太太,才结婚就出门买菜啊,你们家老王也不知道疼人。”
“再疼人,也要吃饭啊,再说了他一个大男人抹不开面子,哪懂砍价啊,现在的蔬菜一天一个价。”
正说着,一群主妇们拎着水灵的茭白青菜从菜场回来了,叽叽喳喳接话说:
“哎吆,青菜都二十块了,还要不要我们老百姓活了,一百元法币以前能买一头牛,五年前能买一头猪,现在只能买点蔬菜鸡蛋,再这样下去,日子真没法过了.”
林秀梅一听这话,脸上一片焦急,连忙抄着菜篮小碎步走了,一群妇女望着她的背影指指点点。
“哎吆,你说好好一个姑娘怎么就看上了一个老男人。”
“话不能这么说,人家老王经营着一家书店呢,是文化人,体面人。”
“呸,文化人值几个钱,政府里头没有人,一样是个穷酸鬼。”
“我家要是有个当官的,一样吃香喝辣.”
这些人的议论林秀梅自然听不见,此刻她已经赶到了闹哄哄人头攒动的农贸市场。
一路挑挑拣拣,讨价还价,终于走到了一个卖鱼的摊位前。
这里不仅有活蹦乱跳的鲜鱼,还有冻成硬块的死鱼。
摊主是一对头发斑驳的老夫妻,看到林秀梅神色微动,热情洋溢地招揽着:
“姑娘,昨天你卖过咱家鱼,不错吧?今天有新鲜的,要不要来一条大的?老主顾了,我给你便宜点。”
林秀梅有些踌躇,皱眉对比着价格,犹豫了一会,还是指着一条冻成硬块的小鱼:
“就这条吧。”
“好勒。”
男摊主手疾眼快,已经将鱼抄起了,过了称,搁置在案板上,三下五除二,就将鱼肢解了,用一个泛黄的荷叶一包:
“刚好五十块。”
林秀梅点点头,从兜里掏出一块手绢,层层剥开,露出一叠整整齐齐的零钱。
她从里面摸出一张,随手递给摊主,神色平静地将装鱼的荷叶放到菜篮里,施施然又去下一个摊位了。
摊主将钱丢入身边的铁盒里,继续弯腰抓鱼叫卖。
过了半个钟头,菜市场的人群渐少,听到一阵指指点点的声音,摊主抬头一看,几个穿着灰布军装的士兵走了过来。
一人腰间配着短枪,一人挑着胆子,里面装着萝卜大葱小米,后面还有两个扛着长枪的士兵,他们衣服的胸前依稀可以看见模糊的“第十八什么团”的字样。
熟悉的人都知道,这是红党办事处的人出来采买了。
周围的人群都好奇地看着议论着指点着,还有两双眼睛在暗处目不转睛地盯着他们的一举一动。
为首的士兵似乎浑然不觉,走到摊位前,看着一个鱼儿扑腾溅水的木盆,问:
“老板,这鱼怎么卖?”
摊主抬眼,笑着说:“这鱼新鲜的很,我早上捕的,按斤算,小的三块,大的五块。”
士兵微微皱眉,轻轻摇头:“太贵了,便宜些。”
“哪里贵了,你们当兵的还差这点钱?”摊主笑着,随手一指盆里的一条死鱼,说:
“这是昨天的,你诚心要,可以给你便宜点。”
边说边用手指轻扣鱼盆边缘,一下,两下,似乎已经迫不及待要抓鱼了。
士兵眼神一闪,瞬间恢复如常,犹豫了一会,摸了摸口袋,最终说:
“好吧,就这条。”
摊主得意一笑,称重剁鱼包裹,狡黠一笑:“50元。”
士兵皱了皱眉:“不是说便宜点吗?怎么还要五十?”
“你要还是不要吧?都说你们红党纪律严明,该不会欺负我一个卖鱼的老头吧?”
摊主冷哼一声,死死盯住他,似乎下一秒他就要喊人了。
士兵嘟囔了一句奸商,不情不愿地从兜里掏出一块银元。
摊主迫不及待地拿了过来,在手上掂了掂,连忙揣入怀中,从零钱盒里拿过一张五十元递了过去。
“给您找零,慢走,欢迎下次再来。”
士兵闷闷不乐地接过钱,抄起鱼走了,几人很快消失在熙熙攘攘的人群中。
人群中两双眼睛的主人对视一眼,一人远远坠在士兵后面继续跟了下去,另一人直接来到了卖鱼的摊位前。
“先生,您卖”摊主话还没有说完,眼睛不由一滞,就见来客冷眼盯着他,还撩起了衣襟,露出一把冰冷的短枪。
“拿过来吧!”
“.什么?”
“刚才客人给你的银元。”这人冷哼一声,“现在不给,我就辛苦一趟,今晚去你家里取。”
摊主深知“去你家里取”这几个字的分量和含义,叹息一声,老老实实将银元递了过去。
见这人犹自不死心的盯着他,他无奈地扯开衣襟,将内兜翻过来给他看,空空如也。
“哼,算你个老东西识相!”这人冷笑一声,郑重地收起银元,走了。
摊主失魂落魄地瘫坐下来,默然无语。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