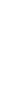武国上都。
金龙盘于玉柱之上,祥凤落霞于檐梁之间,一团金光巍然悬浮在大殿金座上方。
“今,武国携万世神威。四夷秉服,八方来朝,朕当恩泽天下苍生,免生戎马倥偬之苦,拥立仁德义勇之相,免除百万兵丁服役之苦,具留精锐巩卫上都与边疆即可,众爱卿可将兵权交回,威王您以为如何?”一道威严的声音洞穿大殿。
金殿之上,匍匐着数百人,皆是盔甲着身,一副武将打扮,却无一人敢吱声回答。
这武国靠战争立国,从一弹丸之地数十年间扩张了近百倍,依仗的都是这些骁勇善战的猛士,如今天下归一,先帝刚刚逝去,新国君却想杯酒释兵权,将大权独揽,不由得伤了一些老臣之心。
武官之首,匍匐一玉甲老将军,听的国君之言不由得嘴角抽搐一下,一股悲凉之感涌上心头。
他是武国的兵马司元帅,封九千岁威王,跟随先帝南征北战,几乎这武国三分之二的疆土都是他所征战而来的,可谓是功高盖主。
如今天下一统,新君上位,头一件事便是要削藩夺权,身为臣子又有什么办法呢?
自古以来,新君上位,无不以前朝老臣开刀立威,如今却轮到自己头上,金甲将军不由得长叹一声,三呼万岁说到:“臣年事已高,愿交出兵权,解甲归田,望陛下恩典!”
大殿金光之中,新国君不由得嘴角微微上扬,言语之中不由得露出一丝喜色:“威王,您是先帝旧臣,居功甚伟,朕也属实舍不得你的离去,来人呐,赐威王黄金万两,食邑千户,修盖王府一座。”
“吾皇圣明。”威王跪地叩首答道。
朝堂之上,老臣们面面相觑,却又不敢说些什么,只能低头叹息,心中祈求下一个被撸掉实权的不是自己。
转日。
武国上都之内兵马涌动,老百姓好奇的趴在门口观瞧着。
“听说了么?威王昨晚上自缢了!听说是和当今圣……”
一个布衣老汉慌忙捂住了年轻人的嘴巴。
“嘘,不要乱讲,这是要杀头的!”老者带着一丝责怪的语气说到。
大道上的一名禁军犀利的眼神注视着二人,掌中战戈已经悄然立起,一道寒芒闪过,布衣老者与年轻人瞪着差异的目光,脖颈之上一道血丝缓缓流出。
威王府中
白虎堂横梁之上,白绫悬挂着一具早已经冰冷的尸首。
威王临死之前,仍然盔甲着身,早已经泛白的脸上浮现着一丝不甘,却又有一丝解脱的意味。
不久,王府中喊杀声震惊了整个上都,禁军疯狂的屠戮着王府中人,鲜血染红了长空,如血河一般,从王府紧闭的府门中溢出。
“启禀陛下,威王府中上下三万余人,连同家眷奴仆均已屠杀,不过威王幼子却不见踪迹。”
皇宫之中,新皇威严的坐在龙椅之上,手中掐着两颗洁白如玉的念珠,听的下方禁军禀告不由得眉头一皱,一条黑线浮在面颊之上。
“废物!”
新皇一声断呵,手中念珠顿时碎成了糜粉状,从新皇指隙间滑落。
下方金甲禁军吓得立刻匍匐在地,声音颤抖着说到:“小臣立马出兵,翻遍整个上都,也要将这小贼抓到击杀!”
“不用了,爱卿辛苦,拔除威王府有功,早些歇息吧,明日自有人去接替你的工作。”新皇冷冷的说出一句之后便拂袖而去,只留下这金甲禁军匍匐在大殿之上。
冷汗早已经灌满了甲胄,根根汗毛倒立,新皇之言早已经预示了这名禁军的结果。
一道银光一闪而过,带着惊愕之色的头颅落地,还带着余温的金甲无头尸体轰然倒地,只留下一帮小太监手忙脚乱的收拾着大殿上的血迹。
上都之中的屠戮远没有因威王自缢,满门被屠戮而停止。
新皇在朝堂之上不断的威逼功臣,唯一的异姓王威王被新皇满门抄斩,这些剩下的武将们如群龙无首一般,纷纷交出兵权,而一些心怀威王之人均被这新皇用各种手段屠了门庭。
整个上都人心惶惶,均被新皇狠辣的手段所震撼!
距离上都百余里的郊外,一匹枣红色的瘦马飞驰,马上一耄耋老者手持马鞭狠狠的抽打在那匹瘦骨嶙峋的马身之上。
“快点!再快点!”老者似乎疯了一般,手中马鞭轮动,瘦马早已经被打的皮开肉绽,干涸的血迹与枣红色的马毛凝结在一起,刚刚结好的血痂又被马鞭抽开,一股鲜血从伤口中溢出,疼的那瘦马一阵嘶吼。
不眠不休的奔驰了三天三夜,再强健的马匹都会累死,何况这瘦马。
马鞭飞舞,疼的瘦马有些踉跄,脚下不稳,一头便栽倒在地。
马上老者骨碌碌的滚了下来,一块尖石不偏不倚,刚好插在了老者的手腕出,咔嚓一声响动,那只早已经枯黄的老手被折成了九十度,向内弯曲,另一只手却紧紧的抱着一个包袱不曾松开。
外面巨大的响动引得包袱内一阵响动,一声婴儿的啼哭响起,惊得那耄耋老者汗毛倒竖,慌忙解开包袱,用那只还算没有完全折断的枯黄老手轻轻捂住了那婴儿的小嘴。
“小王爷莫要哭泣,我们现在还在危险之地,等逃出上都的范围,老奴就算是死也对得起老王爷了。”
那包袱中的婴儿似乎听懂了一般,硕大的眼睛看着老者,咿呀咿呀的哼叫了两声便陷入了沉睡之中。
老者见小王爷沉睡,慌忙将包裹从新整理好背在身后,一只枯黄的手掌拽了拽倒在地上的枣红色瘦马,却再无一丝动静。
“马儿,马儿快起。”老者呼唤了几声,枣红色瘦马似乎已经断绝了生机,一双马眸早已经暗淡,躺在地上一动不动。
“难道天要亡我威王府后人么?”说着,一股温热的泪水从脸颊上滚落,老者忍着手腕折断的痛苦,踉跄的走了几步,便再也支撑不住,昏死了过去。
郊外断木横生,荒草将瘦马和耄耋老者的尸身淹没,一棵棵参天古树直插云霄,群狼嘶吼,寻着血腥气味而来。
不知不觉中已入深夜,银盘状的皎月悬于高空,撒下点点光亮,透过树木缝隙,一阵躁动声在杂草中响起。
一声声低吼与打斗声此起彼伏。
古树枝桠之上,一个黑袍人注视着下方:“什么响动?”
目光慢慢汇聚在杂草间,不由得让他一惊,只见杂草丛中,一群野狗撕咬着一匹瘦弱的马尸,五脏六腑都被这群畜生掏了出来,鲜血流淌一地,旁边一个枯瘦的老者早已经被吃掉大半,残肢碎片洒落一地,野狗们在撕咬打斗着争抢血肉,身旁一个包裹之中传出婴儿啼哭之声,咿呀作响。
“这是?孩子!”黑袍人定睛仔细观瞧,只见一头野狗的血盆大口已经伸向了那婴儿的脖颈。
嗖!一声破空之音传来,寒光一闪,一口雪白的飞剑从树冠中飞驰而下,不偏不倚,正中野狗的头颅。
由于力道太大,直接将野狗的头颅连同飞剑钉入地面!
这一瞬间的响动惊动了一旁狼吞虎咽的野狗群,一个个停止了撕咬的动作,似乎都愣了一般,直勾勾的看着那只被钉死的野狗。
正当野狗群发愣之时,树冠上的人突然发作,不知何时扯下一大把干枯的枝叶,用火则子点着,猛地跳了下来。
野兽大部分都畏惧火光,先前同伴突然被钉死,现在又有一团火焰从树上猛地跳下,先天的恐惧使得野狗群四散而逃。
“真麻烦,可算都吓走了,这么多狗,老子还真打不过。”黑袍人说着,抖了抖手中燃烧的枯枝败叶,顺手将插在野狗头颅中的飞剑拔出,邋遢的在衣服上蹭了蹭。
“这野狗,真够脏的,可怜我的小小剑,第一次见血居然只是杀了一只野狗。”说罢,黑袍人故作委屈状,摩挲着那柄飞剑,一脸道不尽的心酸,而后他扭头看向了包裹中的婴儿。
那婴儿也停止了哭闹,肉嘟嘟的小脸上沾染了一些血迹,盯着大眼直勾勾看着黑袍人。
“哎,小孩,因为救你,我的飞剑第一次见血只杀了一只野狗!你知不知道,我辛辛苦苦攒了三年才买到可以开光的兵器哎!”
说着黑袍人摘下了头套,露出真容,这是一个还算英俊的男子,明亮的眸子,高挺的鼻梁,厚薄适中的嘴唇,一瞥一笑间似乎还有一颗虎牙。
他拎起包裹中的婴儿,似乎发泄一般,狠狠的揉捏了一下那孩子的小脸,转而又叹息一声:“哎,真是没办法,只能再攒钱了,三年又三年,我俏梨花什么时候能够拥有一把开过血光的神兵啊!”
发泄完以后,他在老者的尸身上摸索着:“好歹我也救了这个孩子,看看你留下了什么能够补偿我的!”
黑袍人自言自语的说着,突然一块玄黑色的虎符从老者的腰间滑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