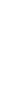孟蝉封的话回响在耳边,孟惠织打了个寒颤,她躺了两天,总算能下地,虽然走路的姿势仍旧奇怪。
前些日子,她把所有书都带回来,每天只背要上的课和作业,免得一个晚上课本就被人乱涂乱画,写些不堪入目的字。
书包很沉,压在她的双肩,迫使她走路更加艰难——她双腿难以并拢,像只鸭子。
中午,等教室的人一窝蜂的涌出,孟惠织慢悠悠前往食堂。
这所私立高中,师资力量强大,设施齐全,游泳馆马场体育馆一应俱全,后山甚至有高尔夫球场。
学校的学生分两种,富二代,或者小康之家,高昂的学费对分数高的学生有免减,大多数富家子弟不会来食堂吃,家庭稍微普通的学生会光顾这里,孟惠织成绩不错,被自动归类到后者。
学习伙食一向不错,打好饭,孟惠织狼吞虎咽,填饱空虚的胃,剩饭也不浪费,装进饭盒。
果然在这,陆渊找到人,心想。
食堂人很少,孟惠织一眼就瞧见高个长腿的他,心里发慌,匆忙吞下最后一口,抹掉嘴角的油,拔腿就跑。
陆渊几步走到她跟前,拦住她的去路。
“喂。”他一伸手,孟惠织条件反射,双肩高耸,脑袋一缩,紧闭双眼。
“啧——”陆渊心里冒火,他有那么恐怖吗,搞得像在欺负她,悬在空中的手垂下,掌心的东西扔到桌面。
“拿着,如果不去,后果自负。”丢下这句话,陆渊立马扭头离开,如果不是颜凌,他才不会找这个丑女。
孟惠织睁开眼,展开桌上的纸条,上面写着一行工整挺拔的小字:“放学和西边器材室见——颜。”
她不知道陆渊口中的后果是什么,但非常清楚不按时回家的后果,还餐盘时,把揉成一团的纸条扔进垃圾桶。
放学后,等人走的差不多了,她背起书包,径直往校门口走去,快保卫处,三个男生突然冒出来,犹如一堵墙,挡在了她面前。
三个人中有张熟面孔,盯着她的目光十分露骨,黄头发,上次在厕所差点奸了她。
“颜少在老地方等你,和我们走一趟吧。”
孟惠织捏紧书包肩带,脚尖一转,一溜烟朝另一个方向跑。
只是她走路都走不好,跑步又能有多快?三个人没费多大力气就追上她,逼着她往器材室走。
西边的器材室废弃多年,门锁生锈,用根铁链拴着,铁链的锁钥匙八百年前就被管理员弄丢,拿个铁钳一夹就开。
孟惠织被他们抓着拉到这个地方,身后的大门“吱呀”关闭,室内光线昏暗,只有又高又窄的透气窗洒进一点夕阳的光线,在落满灰尘的地板上投出篮球大小的金色圆斑。
颜凌坐在半人高的跳马上,左脚点地,右脚支起,脸上挂着平日里如沐春风的笑容,问道:“为什么放学不来?”
往日让她心动不已的笑,此刻却生出一股寒气,她低垂着头,不敢看颜凌:“我家有门禁,我得按时回家。”
颜凌从跳马上下来,一步步逼近孟惠织,弯下腰:“生日那天吃的苦头还不够吗。”
他抬起右手,钳住孟惠织的下巴,欣赏她的侧脸——有着巨大丑陋疤痕的那一面,跟他那只烫脱毛的小猫一样。
“颜同学。”孟惠织闭上眼睛又睁开,极力压下不好的回忆,“如果没什么事,我就先走了。”
她怕下一秒就忍不住揍到颜凌脸上,质问他为什么那样对她,显然,她现在没有打颜凌的资本。
“把衣服脱了。”
“你疯了!”孟惠织拍开颜凌的手,转身就走,伸手推铁门,铁门纹丝不动,拨弄生锈的老式锁栓,怎么弄都打不开,额头直冒汗。
“扒掉她衣服。”颜凌对他的拥护者发号施令。
“你们要干什么?!”感觉到身边逼来的气息,孟惠织仿佛又回到那个小小的厕所,几个黑影围住她,伸手扯她宽松的校服,她只能当鸵鸟,缩起头:“求求你们不要……”
为什么偏偏是他,谁都可以,唯独不想被颜凌这么对待。
黄毛男生格外急切,上次在厕所差点就能睡到孟惠织,结果给教导主任搅黄了。
孟惠织被几只手拖倒,拼命按着自己的衣服,顾上顾不了下,没一会脱的只剩内衣,如同待宰的羔羊,屈辱又难堪的暴露在几道不善的目光里。
身上的痕迹比上次还多,密密麻麻的条状红痕交错在背部,臀部和大腿,十分渗人。
“你还有这种癖好,能赚多少钱。”
孟惠织感觉像被人打了一巴掌,不同于孟禅风那一巴掌,心血淋淋的,仿佛一万根针在扎,她脸色灰白,喃喃道:“我不是……”
“那是谁弄的。”颜凌蹲下来,指尖描绘着她身上的痕迹。
“……”
一直保持微笑的脸冷下来,颜凌勾着孟惠织的内衣扣,轻轻一跳,胸罩脱落,露出的胸肉惨不忍睹,添了几个新鲜的指印。
他站起来,晦暗的目光扫过这几个按着孟惠织的人:“谁先来?”
孟惠织僵硬的躺在那,喉咙发涩,胸口堵得厉害,她闭上眼,把自己想象成一个无趣的性爱娃娃,娃娃是不会痛,不会感到难受的。
修长的手指顺着她的脊椎下滑,仅剩的内裤也脱下,在场的人呼吸陡然变重。
“呜哇哇……求你们……呜呜呜…咳咳……不要……颜凌我、我会听你的话……咳咳我错了……呜哇哇……”心里的弦崩断,孟惠织嚎嚎大哭,她做不到把自己当娃娃,她是人,喜欢的人让别人奸她,心痛的要命,不停抽噎,呼吸不过来,五官拧成一团,眼泪大颗大颗掉到地上,好难过,身体真的好痛,马上要被人奸了,捅她的肚子,搅烂她的穴。
“谁在里面?”陆渊对守在门口的人问。
“颜少,还有赵毅他们几个”
陆渊抬手推门。
“陆少,严少说谁都不能进去。”
“我也不行?”
两人对视一眼,他们知道颜陆二人关系好,颜家是百年豪门,陆家有红色背景,这两人谁也得罪不起,不再作阻拦。
大门露出一条缝,一阵令人心惊的哭嚎溢出来,陆渊赶紧闪身进去关门。
借着透气窗洒进来的光,他看见孟惠织浑身赤裸,内衣内裤摇摇欲坠的挂在身上,被三个人按着,颜凌蹲在她旁边。
“你怎么来了?”颜凌转过头问。
“为什么不能来?”
孟惠织更加凄厉的大叫:“陆同学,救救我!”
她慌不择路,脑袋发昏,向绝不可能救他的人求救。
颜凌笑了一下,示意按着孟惠织的三个人离开,他们不情不愿,又不敢违抗阴晴不定的太子爷,只能离开。
孟惠织跪着,抓着他的裤腿,姿态十分卑微,眉眼皱在一起,本来就丑的脸更加的不堪入目。
“我真的、要早点回去,明天好吗,以后绝对听你的话。”
这副凄惨的模样取悦到了颜凌,他摸了摸孟惠织的头,站起来,弯起眼角:“给你十秒钟,你要是能出去,今天就放过你。”
“10,9,8。”
孟惠织没有任何犹豫,连忙爬着抓自己的衣服,可是陆渊一脚踩住她的外套,用力抽抽不动。
“7,6,5。”
她心一横,朝陆渊一撞,竟然把他撞开,抓住衣服往门口跑,刚才那三人出去,门关上后没有反锁的声音,她的手指碰到锁杆,再拉一下就能打开大门。
“4,3,2。”
门打开了,她甚至看到放哨人惊讶的表情。
“1。”门又合上,一只修长的手越过头顶,抗着孟惠织的推力,毁掉她刚刚燃起的希望。
“你……说话不算数……”孟惠织哽咽着。
“是你输了。”
一股大力抓着她的头发,孟惠织只能顺着力急急后退,倒在一张散发霉味的海绵垫上。
她捂着胸,看着居高临下俯视她的人,他们的脸都藏在阴影当中,看不见表情。
“为什么……要这样对我……为什么?”
回答她的只有解皮带的声音。
疯子,这是跟她的哥哥一样,如出一辙的疯子。
颜凌俯下身,脸凑的很近,孟惠织能感受到他鼻腔喷出的气流,她握紧拳头,冲着那张脸打过去。
手腕立刻被捉住,那只手还在发力,几乎要捏碎她的腕骨。
孟惠织卸力,结结巴巴:“放、放开我。”
颜凌面无表情,十分可怕,她想要后退,可退无可退。
他一手按着孟惠织的双手,一手掏出安全套,牙齿咬着撕开,套在半勃的阴茎上,随便撸了两下,带着本来就有的润滑液,对着热逼插进去。
孟惠织咬着牙不出声,腹部肌肉身紧绷,薄薄的肚皮上凸起一块。
颜凌抬起她的腿搭在肩上,挺动腰部,硕大的性器出入她的腿间,顺着她的手腕摸上去,一根根掰开她嵌入掌心的手指,十指相扣。
“跟你喜欢的人睡,不开心吗?”
好不容易忍回去的泪水一下子流出来,孟惠织望着他漩涡似的眼睛,不明白他怎么能说出这种话。
“滚……”
颜凌轻笑一声,顶到底,感受肉穴的紧致,还有身下人小猫一般破碎的喘息,手指拨开孟惠织黏在额前的刘海,一路向下,划过一道又一道隆起的红痕、可怖的淤青,眼色发沉。
站在一旁的陆渊放出性器,凑到孟惠织嘴边,见她不愿意张嘴,便在她的唇上摩擦,时不时戳她的脸颊,充满羞辱的意味。
孟惠织放空大脑,等他们两个做完,就可以回家了吧。
颜凌释放完,给安全套打上节,扔到一边,陆渊把孟惠织拎起来,抱着肏,刚才不痛不痒的摩擦,早让鸡鸡硬的爆炸,撬开的身体很快就接纳他,感受那片湿热紧致,不停耸动精壮的腰身。
她可真轻,陆渊想着,第一次抱她就觉得她营养不良,个子不矮,但就胸跟屁股有点肉,抽泣的时候能看到突出的肋骨,抱起来做十分方便。
他随母姓,早死的爸是德国人,遗传了深蓝色的眼睛和稍显深邃的面孔,骨架大,练过各种散打、武术,举孟惠织跟举娃娃似的。
“放我走吧……”孟惠织声音虚弱,头搭在他的肩膀上,无力的晃动,现在时间肯定过了,不敢想象回家之后会怎么样。
她缴着肚子,希望陆渊赶紧射出来。
直到地上的光斑消失,陆渊才射出来,他放下孟惠织,掏出一张卡扔到地上:“密码是尾号六位。”
“走了。”
两个人整理好衣服,一前一后离开。
大门关上,孟惠织长出一口气,捡起银行卡,穿上皱巴巴的校服,忍着身上的不适,跑到外面搭车,一看手机,已经7:42了,有2个未接电话,内心一阵绝望。
跑回家,她打开门,放下书包,跪在玄关。
一个穿着贴身的红黑条纹西装,气质成熟,外表一丝不苟的中年男性走下楼梯,挂掉电话:“惠织,为什么又回来晚了?”
孟惠织头埋的很低,一言不发。
男人坐到沙发上,打开电视,调到动物世界的频道:“过来。”
孟惠织膝行到他旁边,屁股压着脚趾,头虚虚的放在他的膝盖上,像只小动物。
两根手指掐着她的脸颊,几乎把她的脸皮揪下来。
“你准备接受哪种惩罚,扇脸,打手,还是打屁股。”
孟惠织抖着手解他的皮带“父亲,我给你舔……”
男人没有阻拦,一双铅灰的眼睛看着电视。
“春天到了,又到了动物交配的季节。”配音解说草原上狮群的交配,雄狮的阴茎长着倒刺,倒刺能刮出其它雄狮的精液,并且困住母狮。
孟惠织握着硕大的、沉甸甸的性器,心一横,一口吞下去,捅进喉咙,眼神飘到父亲的脸上,希望能看到他哪怕一点点高兴的样子。
男人的表情没有任何变化,完全看不出他的女儿给他口交。
大手按住她的后脑勺,往下施力,孟惠织甚至听到了颈骨“咔哧、咔哧”的声音,喉部受到刺激,阵阵反胃,眼泪鼻涕不受控制的流出来。
她不敢有丝毫挣扎,尽力的放松,把这个东西全吃下去,鼻梁陷入黑丛。
大掌握着她的后脑前后摇晃,直到喉咙泛出血腥味,下巴快要脱臼,孟景庭才松开手。
孟惠织一滴不漏的吞下去。
“扇脸,打手,还是打屁股。”
“呃、喝——”孟惠织想求饶,才发现说不出话,她的嗓子磨坏了。
孟蝉封进屋,看见父女二人在客厅,问道:“她什么时候回来的?”
“刚刚。”
两双相似眼睛的对视,迅速错开。
孟蝉封脱下墨绿色风衣,摘掉百达翠丽手表,甩到茶几:“才吃过教训,转眼就忘了,你是在故意惹我生气吗。”
孟惠织双手撑着木地板,浑身颤栗,虽然穿着衣服,却觉得处在寒冬十月,浑身泛起鸡皮疙瘩,恐惧在他的视线里节节攀升。
“啊!”
恐惧爆发了,手特别用力的拉着她的头发,几乎要扯掉头皮,身体摔到地板上,她下意识的卷缩,捂住柔软的腹部。
身上又添了几枚脚印,孟惠织挨打习惯了,还能忍受,可孟蝉封从茶几抽屉掏出来的东西,她不太能忍受。
看上去像情趣用品,但都经过改造,其中手铐是从五金店买。
孟蝉封拿着两副手铐,咔哒两声,将孟惠织的左脚和左手,右脚和右手铐在一起,让她只能保持一幅双腿大开,弓着背部的姿势。
他的脚趾踩着孟惠织的阴唇,那两片可怜巴巴的肉搭在那,因为长期过度使用,颜色很深,逼肿的跟馒头似的,颜色艳红。
“喝…哥……对……求……”每说一个字,喉咙都会冒出一股锈味。
“啊——”孟蝉封狠狠地朝她的逼里踢了一脚,脚拇指嵌进去,孟惠织想捂住,但是手被金属镣铐勒着,嵌出一圈红痕。
裤腰带抽出来,令人窒息的破空声之后,与皮肉接触,发出清脆的声响。
“啊啊啊啊咳咳——”孟惠织在地上翻滚,皮带比藤条长,打人更疼,打过的地方泛出红痕,过不了多久,就会变成一条带深紫斑点的淤痕。
“呜呜呜咳咳……呜啊——”
孟蝉封越打越兴奋,下体高高翘起,扔下皮带,就着干燥的穴插进去。
施暴欲和性欲,孟惠织都能帮他解决,这就是他的妹妹在这个家最大的用处。
“不呜——咿呀——”孟惠织发出令人心惊的哀嚎,完全超出尺寸的肉棒破开穴肉,狠狠的撞在尽头。
好痛,好痛……她大张着嘴,泪流满面,她的逼早就烂了,日复一日的折磨,让伤口迟迟不能愈合,每夜靠止痛药入眠,性器侵入她的阴道,粗糙的表面似无数的小刀,割刮敏感的神经,仿佛含着烧红的铁棍。
腹部深处一阵酸软,孟惠织微微抽搐,孟蝉封的龟头硕大,跟个拳头一样,不断翘她的子宫口,她最怕的就是宫交,每次进去,都让她有种胞宫破裂,灵魂出窍的感觉。
反复的交媾,孟惠织的宫颈很松,孟蝉封轻而易举的插进去,感受那个小肉套吮吸自己的顶端,插到子宫让他很有成就感。
“呃——呜不……”孟惠织双眼上翻,吐出舌头,过量的刺激令大脑过载。
胞宫被撑大,彻底成了孟蝉封的几把套子,他摁着孟惠织的腰,大力的进出,跟打桩机一样,每次都用力的顶到底,身下的人咿咿呀呀的乱叫,戴着的手铐哗啦作响,声音刺耳,这是惩罚,他很清楚,怎样让孟惠织更难受。
囊袋撞击孟惠织的阴蒂,发出啪啪的水声,孟惠织弓着腰,做不出任何保护自己的动作,只能敞开柔软的怀抱,任孟蝉封掠夺。
坐在沙发上的孟景庭动了,他轻拍孟蝉封的肩膀,孟蝉封会意,把孟惠织抱起来,对着父亲。
孟惠织眼睛瞪得像铜铃,惊恐地看着父亲,伸出两根手指往她逼里塞,她含着泪摇头,眼中尽是绝望。
“呜……啊!!!”
两根手指进去,穴口撑到发白,她吃不下……哪怕是操她后面都行!
孟蝉封抽出来一点,留着空隙,父子两人一起挤进去。
太紧了,两人同时想着,脸上青筋鼓起,果然很勉强。
“啊,啊……”
孟惠织浑身瘫软,瞳孔涣散,大脑启动保护机制,分泌肾上腺素减轻痛苦,手脚在空中晃荡,尿液流出,淅淅沥沥滴到地板上,她失禁了,血丝顺着大腿蜿蜒而下。
两个人就着血液和体液的润滑,不断进出,孟惠织趴在孟景庭的肩头,四肢像青蛙一样折迭,如果从背面看去,就像一对关系很好的父女抱在一起。
两根利刃在泥泞的腔道中搅动,孟惠织被夹在中间,叫都叫不出来,乳肉四处乱颤,孟蝉封索性叼着,边吃边干。
一股微凉液体冲进孟惠织子宫,射到肚子鼓胀,孟景庭抽出来,去盥洗室洗澡,他年纪大了,精力不如年轻人。
孟景庭走后,她被孟蝉封压到沙发上,因为手脚铐在一起,只能跟树懒一样抱着他,手脚盘住他的上半身,双乳贴着他的胸肌,像一对亲密的恋人,两颗樱果在胸前反复摩擦,屁股反复吞吃肉棍,夹的孟蝉封欲仙欲死。
快感积累到顶点,孟蝉封抵着孟惠织的子宫射出来,拔出半软的性器,操开的穴口合不拢,没有东西堵住,立刻流出黑红白混合的液体。
肚子以下麻麻木木,孟惠织侧躺在沙发上,连动手指的力气都没有。
只能眼睁睁的,看着孟蝉封拿出她最恐惧的金属夹子,夹子后连着一根线。
“不……咳咳……呜呜……呜不…”孟惠织不断摇头,发出含糊不清的呜咽,嗓子撕裂般的疼痛,说不出完整的话。
“事不过三,这是第二次的教训。”
两个铁夹咬住孟惠织胸前的红点,一块铁片插进她烂的逼里,她只能跟困兽一样,共人虐待取乐。
“啊啊啊!!!”
孟蝉封按下开关,她仿佛被一股巨力击中,双眼陡然睁大,被束缚住的四肢不受控制的剧烈抽搐,双手紧紧握拳,手指因为过度用力而发白,转身掉下沙发,肩膀一阵剧痛,不知道有没有磕断,嘴巴大张,却发不出任何声音,只有喉咙里传出一阵含糊的呜咽,脸上肌肉抽搐,表情极度扭曲,酷似幅世界名画《呐喊》。
骚味从她身下蔓延,她再次失禁,躺在一滩尿液里。
孟景庭从洗手间出来,散着头发,看上去比孟蝉封大不了多少,水珠顺着发梢滴落,水痕延伸到孟惠织身边。
“不要玩的太过火。”
“嗯。”正上头的孟蝉封随口应了一声,看着孟惠织制挣扎的幅度变小,往她身体里塞乱七八糟的东西,前面后面都塞,撑的肚子跟皮球一样大。
心里默默倒数,到了人体极限,他关掉开关,把那些道具抽出来,就着糜烂的穴口捅进去。
半夜,孟惠织被冻醒,她光着身子,身上盖着一件衬衫,镣铐没有打开,钥匙扔在一边。
她翻身,浑身的骨头发出“咯吱”的酸牙声,努力的去勾钥匙,手指木木的,不听使唤。
费了很大的劲,终于打开手铐。
她半爬半跪的进入盥洗室,屁股缝流出来的东西滴了一路,就像糖果屋里,在路上扔面包做标记的小孩。
扶着墙打开花洒,温水带走精液和尿液,瓷砖地面冰凉的温度,给抽痛的下体减轻些许痛苦。
看着邋遢撕裂的阴唇,孟惠织伸出手指,轻轻一碰,刀劈似的痛楚传上来,不住吸着凉气。
她的肚子里没有东西,但是肚皮还在抽动,红肿的肉逼过于敏感,甚至能感受到肉壁内脉搏的跳动。
困意来袭,她实在抵挡不住,晕了一会,头撞到浴缸边缘,一下就清醒了,关掉花洒,爬到洗手池旁,撑着台面站起。
镜子里的人惨不忍睹,身上黑色的巴掌印一层盖着一层,青红条纹交错,膝盖和肘关节完全变色,极其恐怖。
奶子几乎烂掉,耷拉着,跟烂掉的逼很应景。
宛如女鬼,面容丑陋,脸色惨败,身体破烂,她只瞟了一眼,不敢再看,低头扣自己的嗓子眼。
“呕——”
熟悉的反胃之感,喉咙剧烈收缩,又是那股灼烧之痛,沉甸甸的胃反出一口白浊,她吐着舌头,粘糊的液体顺着舌尖拉出长丝,滴到洗手池底。
“呕……呕”看着吐出来的东西,她再也忍受不了,双手扶着池子,大吐特吐,直到胃部阵阵抽搐,打开水龙头,让清洁的水把这些污秽带走。
跪趴着擦干净地板,一手捂着肚子,一手扒着墙向卧室走,十几阶楼梯走走停停,牵扯着各处的肌肉,让她走的十分艰难,每一步,仿佛凌迟。
到达她的小房间,唯一栖身的地方,孟惠织裹上被子,神经陡然松懈,眼前一黑,失去意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