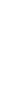十星慕眨眨眼,表达自己的疑惑。
艾尔海森:“帮你降温。”
晚风偏凉,艾尔海森的手掌也透着一种夜色的冷意。
两个人突兀地陷入安静,十星慕的脸庞越来越红。
耳朵向后折了一小截,细细密密的短绒毛轻扫过艾尔海森的掌心,有些痒。
十星慕残存的理智告诉她这样不行,感觉再这么沉默下去事情就有些向失控的边缘发展了。
她偏过头,问:“为什么是雪狐?”
“或许前一天晚上熬夜在旅店窗台前蹲着看雪狐的人不是你。”艾尔海森淡淡道。
十星慕:“。”
十星慕:“我又想起来了。”
对付醉酒的人最好是顺着对方说。艾尔海森扶着她,做出一个愿闻其详的表情。
便听到十星慕斤斤计较起来:“最后一次你接住我的时候,是不是在一个有很多海獭的水域?所以我才会第一次遇见你时,以海獭的形态。”
她的逻辑有点混乱,控诉的意图却很明显。
“严谨一点来说。那时我不知道你,你不认识我。应当是你在碰瓷。”
十星慕眼神乱飘:“……好的。”
“而且降落的地点不是我定的。”艾尔海森却说。
他掏出之前纳西妲递给他的黄金怀表,不知什么时候变成了一个指引方向的罗盘。
“就算你此刻跑到天涯海角,我也可以找到你在哪里。”
说出话的时候他俊朗的五官并没有做出什么表情,艾尔海森一直缺乏表情,而这常常是别人误会他的原因之一。
后半夜的街道没什么人,光影投下一片侵略性的阴影。他恰到好处地保持一定的距离,只有手掌与她的耳朵贴合,就这么专注地与十星慕对视。
十星慕认真地问:“先生,你知道你现在这样子有点像那什么的反派角色吗?”
阴暗的实验家,严谨的疯子,并不在意实验素材的叛逃,他早已布置好天罗地网。
“如果你介意的话。”艾尔海森停顿片刻,才道,“我确实曾在你系在脖子上的金属铭牌里装过定位装置。”
十星慕缓缓地浮现一个问号:“……?”
那是要追溯到教令院的时候,几个愚人众和阿扎尔的残党准备绑架小海獭。
但解释起来又将是一个冗长无趣的故事,而面前这人已做好算账的模样。
艾尔海森懒于解释,干脆空出一只手,抬起她的下颚,俯身去堵住那张想要喋喋不休的嘴。
这个吻带了点敷衍,触感很轻,毕竟初衷仅是让她不要说话。艾尔海森还有闲心去观察十星慕的神情,她海蓝色的眼眸因为错愕而微微睁大。视线再往上,那对耳朵“刷”一下挺得笔直,蓬松得像顶了两颗棉花球。
艾尔海森于是挠了挠那对耳朵。
一阵奇怪的痒意从头顶刺激到她发麻。十星慕忍不住哆嗦了一下,像清晨一滴冰冷的露水从后脖颈滚落到身体里。
加上酒精的催化,她略微有点腿软。整个人像陷在了云里。
很好。看起来十星慕现在忘记了声讨。
艾尔海森从容地把她拎回旅馆,随后妥帖地安置到她房间的小床上。
她睡得很香,脸庞仍然带着一点红晕,安静地闭着眼睛,鸦羽一样的睫毛投下细密的阴影。
像一块易碎的,凝固起来的冰。
艾尔海森看了一会,把窗帘拉好,半蹲在她的床前。
意识模糊中,十星慕感到额头传来一种轻柔的触感。
她梦到了很多年前,一只虔诚的飞鸟曾期许停留片刻。
*
艾尔海森去叫十星慕起床的时候,她正对自己头顶的耳朵无可奈何。整个人看上去感觉像是要成为头发打结的一部分。
“醒了?”艾尔海森走了过来。
十星慕点点头。几缕头发缠过雪白色的耳朵。
难以想象昨晚是一个怎样的睡姿。艾尔海森看了一眼床。
整理得倒很简洁。
早上醒来时,十星慕的手贴合在枕头上,是一个侧躺的姿势,呼吸平缓,一切都是那么的平静。
除了被子整个正反面翻转了。
这些都还好。
但是耳朵。
十星慕叹气:“耳朵还在。”
不过这个世界上还有许多不同耳朵的人。比如她见过的小草神,小可莉,莱依拉,是可爱的精灵耳。昨晚去隔壁酒馆看到一个小小调酒师,迪奥娜,是软乎乎的猫耳朵。
问题不大。
下一刻她便感到脑袋上被戴了个帽子。
宽大的帽沿挡住视线,十星慕往上抬抬,看了一眼艾尔海森,又想起小雪狐的四个爪套,觉得这人是在浪费摩拉:“没有必要吧。”
耳朵都被压得有点瘪。
支棱不起来了。
“金钱之所以具有价值便是因为它能交换物品。”艾尔海森说,“否则只是一个物质。”
多么超前的觉悟。
既然买了,她就戴上了,有样学样地模仿:“帽子之所以具有价值便是因为它能佩戴到脑袋上。否则只是经过特殊裁剪的布料。”
不论艾尔海森到底出怎样的心情买下这个帽子,十星慕戴着它便出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