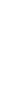这句话落下的时候,突然浮现出萤火虫一样的光点,映照到十星慕湖蓝色的眼眸之中。
艾尔海森略显错愕地仰头,向遥远的天空望去。
旷远的天青色中,几颗新生的星星熠熠生辉。
相当奇异的景象,仿佛星海因为他的一句话而倒转法则。
即使少年人此时的记忆会被抽走,但这转瞬即逝的惊艳永不磨灭。
“你——”艾尔海森讶然,望向十星慕,他谨慎地问,“你是什么生命?”
十星慕笑了一下,她站起来,深渊的裂缝在她的脚底展开。
流星坠向那个缝隙,闪烁的光芒模糊他们之间的距离。
不知从何而来的光点,跨越漫长的时间,汇聚到此处。
但最终她还是什么也没说。
“我吗?”
我目睹过一个复仇的国度如何覆灭。
见证赐予万物新生的神明奔赴既定的灭亡。
我的友人肩负起一个不可能的重任,耗费几百年筹谋自己的牺牲。
复仇的烈火崩溃于瞬息的夜色。
也遇见过一个……不可遗忘的重要之人。
然而所有的这些共处的片段、刹那的记忆和触动的瞬间。
都将湮没于深渊的洪流。
如同冰融化于水中。
*
回响的余光环绕在身边,裹挟着她追溯到风暴的源头。
然而记忆的碎片却拼凑出一个意想不到的人影。
她微微瞪大眼睛。
然而在她辨认出来之前,它们便消散在古堡挽歌的余音里。
一场风暴的止息,仅在呼吸之间。
阒静的海渊悄无声息上涨,形成一道与尘世的隔阂。
一个没有名字,失去许多过往的人,或是精灵,会有一个未来吗?
她仰倒在涩苦的浪潮里,望向水纹之上的钟塔。
“咚——”
它敲响,象征一天的开启。
这时,一张字条漂浮出来,在涟漪中像放飞的风筝。
她接住它。接住这个唯一降落的锚点。
然后她把自己缩成一个自闭的果壳,迷惘地生长在一片盛开着蒲公英的山坡上。
“哎呀,这次的出场造型居然是个苹果吗?”说话也仿佛在吟诗的少年音响起,他弹奏着斐林,蹦出一段跳脱的音符,不满道,“也太狡猾了吧!就不怕我一口把你咬掉吗!”
*
上次见到他时,他还自称巴巴托斯。
这次又换了个名字。
“请称呼我全提瓦特最伟大的吟游诗人——温迪!”
“这么长的称号不嫌麻烦吗?”
“总比你又什么都记不得强吧。我是不是还得跟你庆祝一下,风暴止息后你居然还能记得我……咦?”温迪好奇地凑上前,翠色的帽沿,那朵纯白色的塞西莉亚抖了一下花瓣,“这么说起来的话——你是创造了别的记忆和情感吗?”
她的记忆现在一塌糊涂,闻言茫然道:“啊?”
温迪眯起眼睛。
他抬手,一缕飘渺灵动的风不知从哪翻出一个字条,送到他的掌心。
她皱起好看的眉毛,有一种宝物被人抢了的感觉:“还给我。”
“十星慕。不错不错,你也有名字了。”温迪又念了一遍,琢磨出一些不对劲出来,“喔哟。”
“巴巴托斯在上,请原谅我即将浪费的佳酿。”十星慕缺乏感情地说,“我打赌你埋藏酒瓶的位置还在那几个老地方。”
“哇!是凶巴巴的精灵耶!”
“字条还给我啦!”
鲜红的风车菊呼呼地转动,青翠的草地上仰躺着两只无所事事的人形精灵,懒洋洋地汲取着日光。温迪听完十星慕支离破碎的发言,拨动琴弦:“辛苦了,以后就是一段好好歇息的时光了。”
“现在想起来,我还能安然无恙,真是一个奇迹啊。”十星慕不由自主地感慨。
“是奇迹吗?我不这么觉得哦。”温迪说,“如果理想者的归宿都是这样的话,那太令人难过了吧。”
他指了指那张字条,流露出一个意味深长的微笑。
“所幸,在这场命运严酷的试炼里,有人给你递了一张作弊的小纸条呢。”
十星慕不置可否。
温迪突然坐起来:“要出去走走吗?现在风花节,可是蒙德一个浪漫的节日呢!”
“懒得动。”
“走嘛走嘛,去广场看看?”
十星慕:“我又没有什么可以一起过节的人。”
“诶诶,可不能这么讲。”温迪撑着脸,敛眉思索着什么,“就像人们传颂的一句诗……怎么说来着?”
“谁也没有见过风,更别说我和你了;谁也没有见过爱情,直到有花束抛向自己。”
蒙德城四处悬挂着翠绿浅蓝的缎带,捆绑成花朵的模样,蓬松的蒲公英翱翔在大街小巷之间。酒馆飘来悠远的清香,玻璃酒瓶清脆地碰撞几声。婉转的鸟啼在依偎的恋人上空盘桓,牧歌与自由的清风飘荡。
广场中央巨大的风神像下,已被人献出许多各自心中的风之花。
而温迪说去翻找他珍藏的苹果酿了。
十星慕无聊地支着脸,听着旁人的交谈。